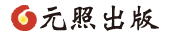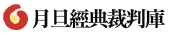醫師急救義務與過失犯理論的耦合(醫法新論)
文章發表:2024/03/20
壹、前 言
依照醫師法第21條規定:「醫師對於危急之病人,應即依其專業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此外,醫療法第60條第1項也規定:「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之急救,並即依其人員及設備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
由前述實定法之規定可以了解,醫師執業時,面對前來求診的病患,必須依照其所在醫療院所之人員、設備、能力予以救治,或是採取必要措施,且不應無故拖延。上段提及分別來自醫療法與醫師法的規定,可認為是廣義醫療法研究中對於醫師急救義務的法源依據。
不過當前醫師的執業環境並不理想,醫病糾紛、診間暴力時有所聞。面對法律規範,找出正確的適用與詮釋路徑,應該是法學研究者對臨床醫療工作者的社會義務。換句話說,法規制定有其脈絡可循,可能制定年代久遠,觀念早已不敷使用;也可能是立法時,立法者根本未能預期到社會風氣變化如此之快,導致法規內容跟不上時代進步,進而面對紛爭時,僅能作出限縮的文義解釋,這樣的態勢除了並不是理想的法律適用方向外,更徒增了醫界對於法律不必要的誤解與抗拒,誠然,這也絕非國家之福。
而向來在廣義的醫療法研究中,醫師的各種義務,諸如轉診、親自診療、告知義務等,都是學者研究的熱區,不過相對而言,醫師的急救義務,則較少引起學者的注目,更遑論為其進行專論。然而,若吾人細觀醫師的養成歷程便不難發現,從希伯克拉底氏之誓詞(Hippocratic Oath)到醫學倫理四原則的上位概念,進而開展到各式實定法中;當醫師面對緊急醫療情況時,幾乎很難想像拒絕伸出援手的情況。
於此,在學術上就會出現幾個需要徹底釐清的問題:首先是醫師的急救義務來源為何?究竟應視為法律之誡命、又或者應該從民事契約法上的強制締約義務進行觀察,進而確立醫師的保證人地位?前述討論,應是本文討論的先決要件。
其次進入具體情境時,則必須關注:醫師的急救義務有沒有界線?而這也是本文在第二個層次所要開展的問題意識—醫師急救義務的適用情境及相關討論。另一方面,縱然醫師有法定的急救義務,但是當醫師違背前述義務時,是否必然構成過失的刑事不法?其論證途徑又應該如操作?這個則是本文嘗試進行另一個面向的討論問題。
故基於前述理由,筆者嘗試對於醫師急救義務進行釋義學的討論,在文章架構上,首先簡述長期以來困擾醫界的過失犯問題,將其發展趨勢以及要件的變化進行簡單的介紹,之後則針對本文所提出的兩個問題意識進行討論,最後做出綜合性的結論。
貳、醫師急救義務的定位與其論辯
如前段所述,依據醫療法第60條第1項與醫師法第21項的規定,似乎可以直觀地認定醫師或醫院對於危急之病患存在急救義務。然而,這項急救義務是如何導論出來的、甚至應如何加以解讀?於學界則存在爭議。
一、強制締約說
採取強制締約說的觀點認為,前述醫療法與醫師法的規定,應從民事契約上進行觀察,並且不應使用「急救義務」的觀點,而應該採民事上強制締約的相關理論加以理解。學者觀點認為,醫師資格屬於國家的特許行業,醫病關係的存在同時也代表著醫療契約的成立。故前述規定似乎應該以契約關係理解較為正確,且注意義務之強度隨之下降,於故意或重大過失情況下方存在法律責任。而違背前述法律規定的效果,應該僅有行政罰與民事損害賠償責任;而不應該納入刑罰解釋的空間。
二、事實上承擔說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對於醫病關係之間,醫師究竟有無對患者有急救義務—亦即是構成刑法上保證人地位,存在獨到的觀點。氏著見解認為,醫師對於患者的生命或身體法義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應該取決於醫師對患者之生命身體,有無事實上的保護功能(tatschliche bernahme von Schutzfunktion)。而所謂事實上的保護功能,則以醫病之間的信賴關係連結,成立時點,可能是醫師對於患者應允治療時,便已經承擔起前述的保護功能;反之,若醫療行為結束,或是患者片面中止醫療關係(例如更換主治醫師),此時醫師就不再對患者存在事實上承擔,同時也不存在保證人地位。
三、本文見解
本文觀點認為,若將醫療法或醫師法的前述規定理解為一種作為義務,事實上便有可能進入刑法上保證人地位的討論,從而在醫師違背前述義務時,將可能面對刑事責任的追究。主張強制締約說的學者在行文脈絡中,可以明確地發現欲排除這類「風險」。
但論者可能沒有考慮到的問題是:縱然改採強制締約說,醫療契約如同論者所言是「被動式」地構成,但在醫療契約中,醫師仍然對患者存在保證人地位,並不可能從法條釋義上,抹去「法定義務」之認識,而改採契約說,就可以免除醫師的刑事不法責任,以筆者之觀點而言,若採強制締約說,反而更穩固了醫師的保證人地位角色,並無法達到學者所期待的免除刑事責任糾纏之目的。是以,筆者認為,強制締約說的觀點,其實對於醫師急救義務的定位,並不存在顯著的效益。
反之,刑法學者提及的「事實上保護功能」觀點,無論是臨床實務或是法律責任的判定上,都存在較高的可操作性。事實上保護功能說所強調的,是擁有保證人地位者對於風險的掌控,故而學者將之帶入醫療法的相關討論時將可以發現,醫病之間的連結關係或許才是判斷基準,而非一律使用契約關係對之加以解讀。舉例而言,患者在三萬英呎高空的飛航過程中心肌梗塞,而同行者有醫師願意協助其排解症狀,此時二者之間就存在信任與連結關係,醫師也會因此承擔起保護功能,並不必然需要透過具象的臨櫃掛號等行為,使用強制締約加以理解。
綜上所述,本文見解認為應採取事實上保護功能說,對我國醫療法第21條與醫師法第60條第1項之醫師急救義務加以理解。不過在此前提之下,筆者與前述學說有著相同的觀點,亦即是醫師縱然處於前述假設的緊急醫療情境下,醫師依舊有拒絕承擔的權利,拒絕之效果應回歸醫療法與醫師法,成立行政罰,此點,本文在後段則會接續論述。
參、刑法之過失犯理論
對於醫師與醫療人員而言,秉持對生命的尊重而付出的努力,卻仍然不能免除負面醫療結果的風險,已經是難以承受之重;但當代社會下,基於種種複雜成因與病人自主意識抬頭的現狀,或許更難承受的是:基於拯救生命的良善初衷,卻要接受法律的檢視,甚至以犯罪行為的「過失」論處。
任何一位理性的社會公民都會相信:沒有醫師會樂見醫療行為發生失敗的結果。但另一方面也難以規避的問題是:在社會契約論之下,國家的秩序透過法律加以維持,當出現紛爭時,法律成為人民之間解決爭議的機制與標準。或許更精確地說,縱然醫療行為的立意絕對良善,兩造當事人也絕對不可能樂見負面的醫療結果,但醫療行為畢竟有其風險性與不確定性的特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除了紛爭難以避免之外,病患或其家屬興訟,卻也是國家賦予所有公民的基本人權,因此,在當代醫療環境之下,醫師如何理解臨床工作風險之所在,以及法律規定與相關理論,應該如何處理醫師的過失行為,就成為整個社會必須直面的重要課題。
就此,本文將在這個段落簡單地從刑法研究中的過失犯理論進行回顧與淺介,由早期的古典過失犯見解,至近年來學者將論著重點,轉而置於「創造法所不容許風險」的見解進行回顧,透過對於過失犯理論的演進,將有助於本文處理醫師在違反法定義務—特別是本文所欲討論的急救義務時,應如何理解其在過失犯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法學論證的應有的重心。
一、古典過失犯見解
古典過失犯理論發展甚早,在論證上強調行為人欠缺注意的心理狀態,故成立過失犯罪之要素為:法益侵害結果之發生、行為人欠缺注意、以及前述二要件之間存在因果關係。而關於行為人欠缺注意之部分,係以行為人「注意義務之違反」與「有無預見法益侵害之可能性」、以及過失是屬於一種罪責型態等觀點。
換言之,若行為人對於法益侵害之結果無預見可能性時,即不成立過失犯罪,但相對的,於行為人有預見可能性時,便成立過失犯。從前述邏輯可知,傳統過失犯理論側重於行為人於「主觀上」對於法益遭受侵害之預見可能性,然而此種架構,學者認為隨著社會演進,各類工商、醫療、交通活動發達,已不足以應付現今社會,早已不合時宜,而有另尋其他解釋途徑之必要。
二、新過失犯見解
依循學者對於傳統過失犯理論的批評,新過失犯理論於20世紀初期逐漸成形。與傳統過失犯理論不同之處在於:新過失犯理論並不僅止於關心行為人主觀的認知,更強調其在客觀上「避免結果發生」之義務,學者有謂「避免結果發生之義務」係新過失犯之理論中心,使過失犯之理論系統由傳統之純然主觀因素,導入了客觀之避免結果發生義務,並且產生了本質上的丕變。
我國學者則認為,新過失犯的理論出現,反映了社會生活型態的演變,由於過往的古典過失犯理論,將論證重心擺在預見可能性,然而,在現今社會中,吾人對於許多新興科技所帶來的活動內容都有預見可能性,如此一來,則會使得過失犯的處罰範圍過廣,反而擴張了過失犯的適用範圍。因此,新過失犯的理論則轉向於行為人是否採取了有效的避險措施,而避險措施所帶來的迴避義務,則應納入預見可能性的內涵當中。
至此,過失犯理論已非古典理論下僅限於罪責層次的問題,而必須同時涉及構成要件層次之雙重審查標準。故而在新過失犯的體系之下,過失犯之成立必須區分不法層次與罪責層次的問題,於構成要件層次應檢視行為人是否在客觀上有預見實害發生之可能性、行為人是否違反了客觀注意義務,並製造了法所不允許之風險、且其注意義務之違反與法益侵害之間具有因果關係。罪責層次則檢視行為人之主觀上有無預見實害發生之可能性、以及依照其個人標準有無違反主觀的注意義務。而前述新過失犯之成立架構,亦成為我國目前之通說見解......
全文刊登於月旦醫事法報告,第86期:長照法制的未竟之路 訂閱優惠
- 中草藥安全別輕忽:天然之下的法律風險 1/2
- AI醫療的倫理規範與責任釐清 12/8
- 醫療器材管理法的制度革新與風險治理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