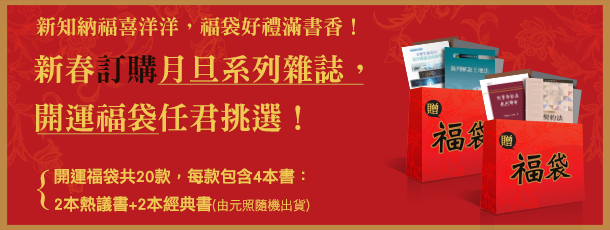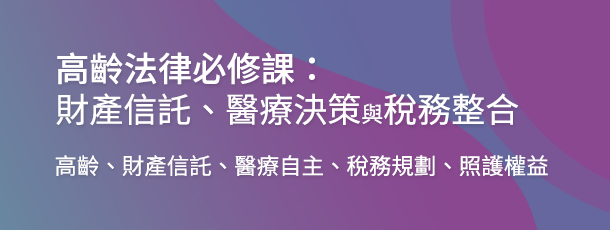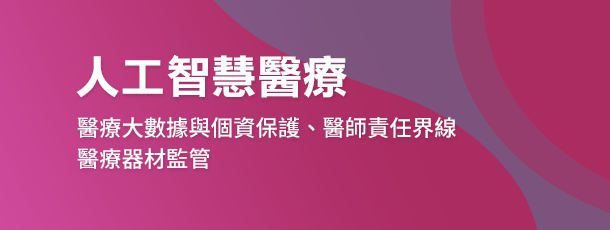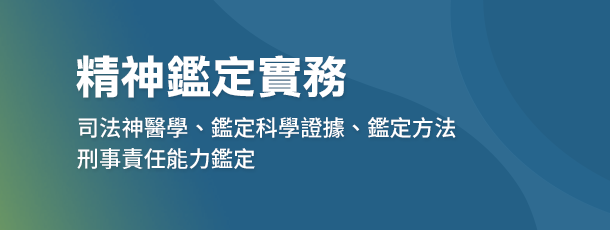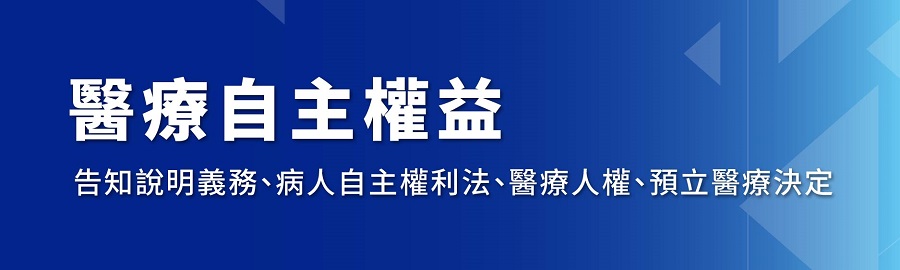敘事與敘事調解(實務講座)
文章發表:2022/09/02
人體內至少有兩種自我:經驗自我(experiencing self)與敘事自我(narrating self)。經驗自我是我們每刻的意識,並沒有深刻的記憶力;敘事自我是負責喚起記憶、說故事、作重大決定,猶如M. Gazzaniga所說的左腦翻譯人員,忙著將過去的絲絲縷縷,編織成一篇故事,並為未來制定計畫。敘事自我對經驗下判斷時,會採用「峰終法則」(peak-end rule),不在乎時間持續的長短,只在意時間的高峰和終點,再加以平均,作為整個經驗價值。
也因為如此,敘事是可以被改變、被重寫的。1990年代,心理學家Kahneman和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的D. Redelmeier醫師合作,對大腸鏡檢查的病人不舒服感覺改善的建議,其結論認為:醫師最好在檢查最後,安排幾分鐘原本不必要的鈍痛(dull pain),如此會讓整個事件的痛苦記憶大減。
正因為敘事解讀的作用,每個人的故事經常帶有自己想像與解讀的成分在內。而對一個想像的故事作出的犧牲越多,就可能越是堅持,只為了讓一切的犧牲和痛苦有意義。在受害者與受害家屬中,這種堅持是很常見的,只有透過受苦才能讓自己的罪惡感得到救贖;抑或是一種心理上的逃避,唯有把自己當受害者,怪罪他人,才不需要面對這種無法承受的沉痛。
敘事調解是以敘事心理諮商為基礎,後發展為敘事醫學所運用,再到敘事調解的提倡。敘事調解是一種講故事的過程,在講故事的過程中邁向和解。在調解的類型中,敘事調解屬於治療型調解,是相對於討價還價式調解的類型。敘事調解的目標代表了混合問題解決導向與轉換型導向(賦權、認可、尋求社會正義).....
全文刊登於月旦醫事法報告,第18期:我的身體誰作主—生育自主與優生保健 訂閱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