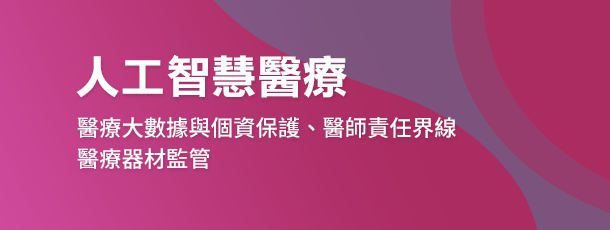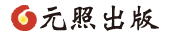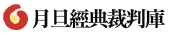道歉制度在醫療糾紛解決中的功效
文章發表:2017/09/05
《医学与哲学》晏英
20世纪也被称为“道歉的世纪”,“公共道歉”最初出现在政治或政府行为领域。当时,一些国家、政府或者公共团体对于曾经的历史错误,会以“公共道歉”方式来表达沉痛反省后的是非观、价值观。在这一政治风潮之下,长期以来,被认为法律不宜介入的领域——人的内心世界,在普通法国家的法域里发现了道歉法的身影。普通法国家道歉法诞生至今不过三十年,尽管余留的一系列课题还有待研究,但为了激励当事者主动道歉,通过切断赔礼道歉与自认行为在诉讼活动中的关联来缩小赔礼道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其发挥的纠纷解决功效已为世人所公认。
1 域外道歉法制度概述
早在1986年12月,马萨诸塞州就为赔礼道歉开辟了一个“安全港”(Safe-Harbor)1通过了禁止在民事诉讼中将道歉的言行作为证据来证明负有责任的法案,马萨诸塞州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设立道歉法的州。
随后,德克萨斯州在1999年通过了该州的道歉法,与前者不同的是,德克萨斯州否定了对于过错承认的保护,并没有对赔礼道歉进行完整豁免。到目前为止,在美国的3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或通过判例法形式确立了对赔礼道歉的保护,或出台了赔礼道歉证据豁免法案2。
加拿大作为一个素以崇尚和平而著名的国家,致力于为道歉的立法,在2006年通过了最早一部省级“道歉法”,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道歉法案》,规定道歉言辞不作为证据呈上法庭。截至2013年4月,在加拿大的10个省、3个地区中已有8个省、1个地区陆续通过了“道歉法”。此外,加拿大还在酝酿如何在联邦层面通过全国统一的《联邦道歉法》,以期适用于加拿大全国的民事法领域,但迄今尚未实现。
澳大利亚早年由于医疗诉讼索要巨额保险费,导致医疗保险费有增无减。澳大利亚卫生部长咨询委员会(Australian Health Ministers’ Advisory Council)认为要减少保险费和赔偿,可由降低诉讼机会入手,道歉正是其中一种可行方式3。现在,澳大利亚的全部6个州和2个领地均已制定了道歉法4。
此外,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诉讼委员会专门授权卫生国务秘书设立必要程序,除提供优惠补偿外,还包括给予必要的解释、道歉和关于已采取行动或者将采取行动以防止出现类似情况的报告,以期“鼓励”国民保健机构向患者做出解释和道歉。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亦有意制定“道歉法”5。
道歉法可分为部分道歉法和完全道歉法,部分道歉法所保护的仅限于同情、遗憾或者安慰,而完全道歉法在部分道歉法的基础上,将承认过失和责任也纳入保护范围。出于对过度保护赔礼道歉可能诱发欺诈性道歉等问题的担忧,对于完全赔礼道歉的立法保护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庆幸的是,实证数据表明,普通法国家实施道歉法减少了医疗纠纷的发生。据约翰·霍普金斯儿童中心的律师估算,从2001年制定鼓励医生公开披露错误并作出道歉的正式政策开始,诉讼的赔偿数额已经下降了30%,因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欣赏(该机构的)坦诚和豪爽”6肯塔基州莱克星敦的退伍军人事务医学中心建立了道歉以及公开披露制度,在1987年实施该制度后,医院报告称:和其他同类医院相比,该院支出的医疗损害赔偿数额达到了最低四分位数,到1996年每项诉讼的责任也降到倒数第六位7。整体而言,不论是部分道歉抑或完全道歉,实施医师道歉制度的州比没有实施的州,医疗纠纷案件的和解率都有所提高,而死亡或四肢瘫痪等重大医疗伤害案件的和解金额平均下降了14%~17%8。
2 道歉法的四大特有功能
从上文可见,普通法国家的道歉法内容主要是切断了道歉与相关不当事实之间的责任关联,并在当事者自行解决医疗纠纷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可是,在我国民众对道歉在医疗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却怀有很深的忧虑9。
普通法国家的这些道歉法实践足以表明其在医疗纠纷解决中有着强大生命力,这是因为道歉法契合了医疗纠纷解决的四个独特条件。这四个条件也正好反映了当下我国医疗纠纷解决中的不足。
2.1 满足了医疗纠纷解决中感情慰藉的需要
在民事侵权行为中,不仅是经济利益遭受到损害,受害人的精神层面同样受到了伤害。可是,由于世界各国大多把金钱赔偿视为民事法律责任承担的最主要方式,金钱赔偿似乎成为了唯一的救济手段。对于医疗纠纷,法律上的所谓责任都只限于经济赔偿。不管是医疗诉讼还是调解,都重在强调法律责任,而所谓的法律责任往往仅限于金钱的赔偿。
但是,作为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与其他事故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一样,大多数的主张都不是为了钱,因为金钱换不回健康或者亲人。很多受害者都强调“这不只是金钱的问题”。这句话说明生命和健康是金钱换不来的,吐露了患方对亲人失去生命或健康的无比痛楚,也是对外界所认为的“人死了赔钱就是了”态度的一种坚决否定。这就表明:具有直接情感抚慰功能的非经济补救方式具有强大的社会需求,而赔礼道歉就是最常适用的非经济补救手段。
2.2 满足了医疗纠纷解决中修复社会关系的需要
赔礼道歉的道德来源在于人的内疚感,或者说负罪感。“当我们没有遵照道德原则之要求去做,抑或做了道德原则要求所不容许之事时,我们通常会对此感到有负罪感。”10负罪感会由于意识到过去不当行为导致的后果而产生羞愧、痛苦,形成对行为人内心的巨大折磨,即“心罚”。就像成语“刮肠洗胃”所描述的那样,“心罚”给人带来的折磨有时远比刑罚可怕。
赔礼道歉能够排遣施害人的负罪感。这是因为,一方面,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希望医疗事故发生,赔礼道歉可以敦促施害人思想觉醒、良知回归,并为该负罪感提供释放渠道。另一方面,对于施害人的真诚悔过,大多数受害人都能给予不同程度的理解甚至宽恕,而受害人的宽恕和理解对施害人负罪感的解除起着积极作用,能让施害人进一步获得内心之平静。
2.3 满足了医疗纠纷解决中把医疗过错看作是系统性问题的需要
在经由法律手段来解决医疗纠纷的构造中,通常将医疗事故发生的原因归责于作为施害者的医护人员个人身上,根本看不到对医疗系统的改善策略。然而事实上,大多数医疗过错以及医疗事故都发生在组织化运作的医院中。像输液这样单纯的医疗行为,有时候也需要数名医护人员参与执行。
过去15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尽管归责文化日趋严厉,但仍有3%~16%医疗不良事件发生,而且在这些不良事件中高达半数都是由可以避免的医疗过错而产生的11。因此,一种崭新的医疗安全文化开始形成:不再拘泥于谁(who)对谁错,而是聚焦于医疗过错何以(why)会发生,以及如何(how)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错误公开及坦诚面对,被认为是预防医疗过错的关键。其背后的理念是,通常愿意面对错误的人,同时也代表有改正错误的意愿。因此,在诸多预防医疗不良事件及促进医疗安全的策略中,鼓励医院和医护人员公开、诚实地面对医疗过程中产生的错误,被视为发现及预防医疗过错的重要基础。
2.4 满足了医疗纠纷解决中达成和解的需要
医疗行为常常在密室中进行,无第三者见证,外人很难判断行为的好坏。再加上,人们面对亲人或者身边的人去世时,即使是自然死亡,也会很想知道他是怎样死的、痛不痛苦等“死亡时的情景”,以及为何会死等直接的“死亡原因”,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因此,在医患沟通中,受害方所追求的正是这种意思下的“事实真相”。这时,如果医方对患方避而不见,对这一诉求置之不理的话,只会加深患方的疑虑与愤怒。
患方在与医方沟通的过程中,在不断评估医方的真诚程度和应对机制。当患方一时得不到“事实真相”时,患方就很“气”,就要“讨说法”。而赔礼道歉恰好为受害方发泄怨“气”提供了一条便捷途径。这样,既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也避免了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节约了司法资源。相反,如果没有进行赔礼道歉,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诉讼争端。
3 医疗纠纷处理中中国与域外道歉的差异
人们通常认为赔钱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但研究表明,通常受医疗伤害的患者更多地着眼于“理”而非“钱”,赔礼道歉,作出解释并提出改进措施,能够化解患者的忧虑并进而避免诉讼的发生。可是在我国,不少医生在医疗纠纷处理中三缄其口:拒不沟通、拒不解释、拒不道歉,从而错过了安抚患者情绪、缓和对立和化解矛盾的有利时机。有些医院即使存在医疗过失,几经交涉,仍然拒绝向患者道歉12,尽早向患者道歉的做法更是遭到非难13。
相比西方正在医疗领域迅速推行的“道歉法”,我国在医疗领域的推行将面临更多的障碍。下文将在与普通法国家的道歉法的差异对比中,分析我国医疗领域中的赔礼道歉所面临的系列问题。
3.1 普通法国家的道歉法更多作为纠纷解决方式,而在我国主要作为责任承担形式
作为法律责任承担方式,强制赔礼道歉在中国的入法,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丰厚的近现代司法实践基础14。这是我国的一大创举,此后,赔礼道歉兼具了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属性,转变为可以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之一。与此对比,在大多数国家,赔礼道歉并不是一种民事责任承担方式。
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的十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中,“赔礼道歉”位列其中,并在第一百二十条特别强调,当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抑或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2009年颁行的《侵权责任法》承袭了《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再次确认了赔礼道歉作为侵权责任承担方式。而《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后,成为了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法律,其中适用医疗侵权的包括赔偿损失、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停止侵害。
纵观西方,古罗马法中没有关于赔礼道歉的相关规定。但是,中世纪后,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陆续制定了赔礼道歉制度。可是,到了19世纪,在各国的司法改革中赔礼道歉制度逐步被弃置。认为赔礼道歉制度与《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原则相违背,涉嫌违宪,被认为是被弃置的最主要原因。因此,一直没有相关规定。
近年来,西方国家开始珍视东方文化中和谐安定的一面,将道歉这一道德范畴要素入法,目的不在于将赔礼道歉法律化,即从道德责任的承担方式通过法律确认转化为法律责任承担方式,而是在于清除良心发现的外部障碍,切断道德成为自认证据的关联。普通法国家希望通过鼓励赔礼道歉来定纷止诉。
3.2 鼓励主动道歉与强制实施赔礼道歉的区别
在我国道歉可以强制,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而普通法国家的道歉法要求致歉方主动道歉。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法院可以通过判决强制被告人赔礼道歉,即所谓的“强制赔礼道歉”。由于我国古代十分讲求礼法秩序,出礼入刑的规范和理念为赔礼道歉作为一种责任承担方式提供了生存土壤,于是,建国后在构建我国的法律责任体系时,立法者承袭了这一传统。由此引出的立法困境也各不相同。前者是道德困境和执行困境,而后者则是保护范围大小的困境。
我国道歉制度的道德困境在于:法律与道德虽然都属于行为规范范畴,但各自有其特定的应用领域、实现机制及作用方式等。虽然某些道德规范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法律化,但并非所有的道德规范都能转化为法律规范。包含赔礼道歉在内的各种道德向善不能由法律来强制,而只能是基于内心的自由选择。我国道歉制度的另一个困境是执行困境。它指的是,很多案件的当事方,包括医院,他们对于是非争端的态度是:“赔钱可以,绝不道歉!”15在这一种情况下,当事者拒绝执行强制赔礼道歉这一判决。法院只能登报公布判决书,登报的广告费用由侵害人承担。赔礼道歉的强制执行被扭曲为采取登报公布判决书的形式,这不过是判决书的再次公布,既然已经公布,再次公布又如何能起到赔礼道歉的效果呢?该形式只不过是多出了一份登报费,道歉的实质无从实现。而且,公布判决书只能起到澄清事实的作用,与道歉风马牛不相及。
而普通法国家保护范围大小的争论体现在:如果道歉法所保护的仅是部分道歉(partial apology),即仅包含同情与善意之表达而不包含任何有关过错和责任的表示,那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符合道歉的定义,因为心理学家或伦理学家认为:一个真正的道歉,是道歉者必须在没有任何借口下,承认其行为不当并表示悔恨,所以没有必要立法进行部分保护16。针对完全道歉(full apology),有学者认为如果道歉不再承担固有的法律风险,那么道歉在道德层面上的意义将被法律架空,道歉法将使道歉成为谋求和解的一种策略17。
3.3 我国有关道歉制度的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3.3.1 道歉在医疗纠纷解决的形式功效未被重视
如前所述,普通法国家的道歉重在程序法方面,切断了在医疗诉讼过程中赔礼道歉与自认行为的关联。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它为医务人员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作出赔礼道歉彻底扫除了障碍,让其无后顾之忧。在医疗领域推行“道歉法”是大势所趋。我国法律也可以增加相应的规定,诉讼中医务人员所作出的赔礼道歉不构成自认,不得作为证据被法院所采信。
此外,我国应该重视道歉的形式功效。中国人在道歉问题上,坚持对与错的原则,认为某些场合下的道歉,意味着承认自己的过失,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可是,不容忽视的是,道歉存在着形式和功能两个方面。形式指外化的表达方式,最常用的是语言形式,如“对不起”、“请原谅”等。功能是指通过叙事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一目的被奥斯汀称为“语力”,如后悔、保证、忏悔等。道歉的形式和功能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有时就仅有道歉的形式而没有道歉的功能。例如,在西方,当听到别人遭遇不幸时,人们常常会说“I am sorry”,都是以道歉的形式表达对对方的理解、同情而非表达歉意。当双方的平衡关系被打破,致歉者希望修复这种平衡时,就会选择以道歉来增强对方对事物的控制感,给对方以心理补偿。
即使是在东方“面子文化”背景中,功利性道歉对受害人“面子”的维护也有现实价值。人的天性使得受害人的愤恨态度非但不能被压制,反而应在制度上提供一种合理的途径以利其进行表达。心理学家的研究已经证实,即使是一个违心的、并不真诚的道歉,也能发泄受害人的怨恨18。
3.3.2 强制赔礼道歉违反了良心自由
《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让它成为了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法律,其中适用医疗侵权的包括强制赔礼道歉。关于我国强制赔礼道歉制度,学界很少注意的一点是:良心自由具有绝对保护属性,因而强制赔礼道歉违反了良心自由。
《日本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思想及良心的自由,不得侵犯。”日本宪法学者解释道,“绝对保障,不管任何理由,一切限制都不允许的自由”,接着指出其包括禁止国家权力的思想钳制、禁止因为思想而加诸的各种不利对待、沉默的自由等19。
有中国学者认为,“我国宪法并未对良心自由作出明文规定,较为接近的言论自由作为一种表达的自由也无法涵盖这一内容”,所以,强制赔礼道歉并不违宪20。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而人权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良心自由2181。“用判决的形式来判令当事者对外表明对有关事物的是非辨别,或者强制对外公开谢罪、道歉等伦理性表述,是侵犯了良心自由的违宪行为。这种反对意见也记录在判决书里。对此表示支持的学说也颇为有力。”21140-141因此,赔礼道歉的道德基础是人的愧疚感,最终源自人的内在良心,强制执行则必然会违反在价值位阶上高于被害人诉讼目的且更具根本利益的良心自由,从而丧失正当性。
“不承认人民享有良心自由,个人的主体性将成为国家祭坛上的牺牲品。”强制赔礼道歉不是对施害人人格的尊重,而是对其人格的否定。一个人格可以被公权力否定的社会,很难培养大多数国民具有独立心的道德,也就奢谈建设一个良好有序的公民社会。
4 对我国医疗卫生基本法中设立道歉制度的立法启示
如前所述,在我国医疗卫生基本法中的引入将对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有着独特功能。我国有着将赔礼道歉入法的传统,但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在我国正在抓紧制定医疗卫生基本法的当下,如何将域外的道歉法与我国的赔礼道歉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植入我国未来的医疗卫生基本法中,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多年的赔礼道歉立法经验,就医疗卫生基本法中的植入兹提出以下立法构想:(1)设立“道歉制度”专条;(2)取消强制赔礼道歉;(3)设立完全道歉机制;(4)侵权人作出赔礼道歉后,侵权人不得因为道歉行为减轻或增加责任;(5)明确道歉免责原则不适用于刑事或重大恶性刑事案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承袭赔礼道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立法传统,尤其是优化配置其在医疗纠纷调解领域中的运用,重新定位道歉法在医疗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使得这一具有悠久传统的道德仪式能够在司法体系中逐步和谐发展。放弃苛严的归责文化并不意味着要正当化过错,而是希望通过“真诚”而非一律谴责,让非故意或重大过失引发的医疗事故的被害者和引发事故的医护人员可以从中得到援助。
第二,“有人就提倡了良心自由观念,以为信仰是自愿的,而非可以强制的事,良心自由当超越于对国家的一切义务之上。”[22]传统社会中的“礼法”在当代并非没有价值,但以司法力量来强制赔礼道歉,超出了司法界限,是对人格的侮辱和对表达自由的抑制,严重地违反了良心自由原则,也败坏了道德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取消强制赔礼道歉可以解除道歉机制在我国现行立法上的法理学冲突,将其从司法实践的死胡同中解救出来。
另外,普通法国家道歉法中的道歉通常指向诉讼前或者判决前,这样的道歉将成为纠纷解决的催化剂;而中国司法中的道歉显露于判决后,判决前和诉讼中的道歉反而不被彰显。我国道歉立法应逐步收缩,从无所不能的责任承担形式退回到诉前或诉中道歉方的自省与悔恨,使司法的归司法,道德的归道德。
第三,法律中的此项设定打破了侵权人道歉和其法律上自认行为的因果关联,解除侵权人道歉的后顾之忧,可为施害人真心悔过提供道德压力、正当性及正式表达的机会。健康的守法心态,其实质内容主要是对法律遵守的义务感和对违反法律的羞耻心23。不与责任成立相关联的道歉将不忌讳承认错误,是自愿、真诚和彻底的道歉和悔罪,能够起到化解纠纷、弥合人际裂痕的作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医学中的错误可能并将继续出现。构建不良事件和人因错误影响最小的医疗系统和环境是基本的,也是可达的。当不良事件的报告文化从责罚转变为理解错误并从中学习时,患者安全的改善工作才可能得以开展。
第四,为了激励侵权人主动道歉,通过赔礼道歉来减轻责任,这在英美法中有例可循。1843年,英国制定的《诽谤法》就已经对赔礼道歉可以作为减轻赔偿责任的依据做出了明文规定,但在我国不宜采用,此项规定衡平了第三条的规定。
第五,不要将道歉这一体现道德的行为扭曲成一种非道德的、功利行为。功利的赔礼道歉——完全道歉机制一般不能适用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严重刑事案件,更不能适用于情节十分恶劣、后果十分严重、民愤极大的重大刑事案件。这一点主要是从目前我国的司法现状出发,以削减反对者的疑虑,减少立法障碍。
人人都有可能犯错,并不是所有的过错都需要指责。面对医疗不良事件,唯有医护人员放下防御心理,坦诚揭露过错,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最终患者才能获得安全、安心的医疗服务。将完全道歉机制入法,重现道歉这一道社会文化现象的光芒,或将有助于我国走出医疗纠纷危机。
參考文獻
- TAFTL.WhenMore than Sorry Matters[J].Pepperdine Dispute Resolution LJ,2013,13(1):181-204. 返回內文
- 陈学德,黄钰瑛.美国道歉制度沿革及启示:告別对立走向对话:医疗纠纷处理新思维:二[M].台北:元照出版社,2014:38. 返回內文
- VINES P.Apologiesand Civil Liability in the UK:A View FromElsewhere[J].Edinburgh LRev,2008,12(2):200-230. 返回內文
- 林暖暖.普通法国家道歉法及其在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EB/OL].(2015-12-07)[2016-02-23].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FullText.aspx?ArticleId=93970. 返回內文
- 香港商报网.林郑月娥指明年初会就道歉法再展开谘询[EB/OL].(2015-12-16)[2016-02-23].http://www.weibo.com/p/1001603920688128893558?from=page_100206_profile&wvr=6&mod=wenzhangmod. 返回內文
- ZIMMERMAN R.Doctors New Tool to Fight Lawsuits: Saying‘Im Sorry’.Malpracticeinsurers find owning up to errors soothes patient anger.‘The risks areextraordinary[J].Journalof the Oklahoma State Medical Association,2004,97(6):245. 返回內文
- RUBEL-SIEDER R.fulldisclosure:an alternative to litigation[J].Santa Clara LRev,2008,48(2):473-506. 返回內文
- HO B,LIU E.Doessorry work ? the impact of apology law on medical malpractice[J].JRiskUncertain,2011,43(2):141-167. 返回內文
- 王夏玲.“道歉”是否有助于处理医疗纠纷?[J].中国社区医师,2012(17):24. 返回內文
- BOND EJ.Ethics andHuman Well-being, Blackwell Publishers,1996:185. 返回內文
- 杨秀儀,黄钰瑛.当法律遇见医疗:医疗纠纷立法论上的两个主张[J].司法新声,2015(7):7-31. 返回內文
- 朱晋.医院疏忽配错胰岛素患者交涉仍拒不道歉[N].南方日报,2012-04-24(A04). 返回內文
- 任之.医疗纠纷不是道歉能解决的[J].中国医学文摘:内科学,2006,7(2):165. 返回內文
- 黄忠.一个被遗忘的“东方经验”:再论赔礼道歉的法律化[J].政法论坛2015,33(4):115-128. 返回內文
- 梅天磬.医院将死者死亡时间“提前”4天只纠错不提道歉[EB/OL].沈阳晚报,(2013-10-11)[2016-02-01]. 返回內文
- SCHNEIDERC D.What It Means To Be Sorry: The Power Of Apology In Mediation[J].Conflict ResolutionQuarterly,2010,17(3):265-280. 返回內文
- O’HARAE A.Apology and thick trust:what spouse abusers and negligent doctors mighthave in common[J].Chicago-Kent LRev,2004,79:1055-1089. 返回內文
- BennettM,DewberryC.“Ive said l’m sorry, haven’t I?” A Study of the Identity Implications andConstraints that Apologies Create for Their Recipients[J].CurrentPsychology,1994,13(1):10-20. 返回內文
- 浦部法穗.全訂憲法学教室[M].東京:日本評論社,2001:123-130. 返回內文
- 王竹.赔礼道歉民事责任方式的源流、承担与执行研究[EB/OL]. [2016-02-01]. http://cc.scu.edu.cn/G2S/Template/View.aspx?courseId=1919&topMenuId=161646&action=view&type=&name=&menuType=1&curfolid=215034. 返回內文
- 芦部信喜.憲法:新版[M].補訂版.東京:岩波書店,1998. 返回內文
- J. B. 伯里.思想自由史[M].宋桂煌译,余星校.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0. 返回內文
- 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关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协调发展的哲学思考[J].法商研究,1998(2):3-8. 返回內文
- 資料來源:域外道歉制度在医疗纠纷解决中的功能及立法启示”,载于《医学与哲学》2017年第38第8A 期(总第578期),第66页-70页。
- 作者:晏英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西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