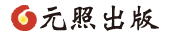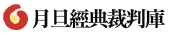美國醫師道歉制度及其對證據法的影響
文章發表:2017/08/23
王丽莎
编者按:
昨日,山东医闹事件中公安局长被免职,卫计委主任被处理,医院30万赔偿款被追回,在朋友圈中刷屏了。对于故意伤害、甚至杀害医务人员的行为,当然必须严厉打击!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都是不可侵犯的。不过,医闹事件愈演愈烈,真的是只靠严厉打击就可以解决吗?刑罚能否发挥其被期许的作用呢?我不知道。只是在代理医疗损害纠纷案件的实际过程中,一是遭遇过基层法院立案难,2015年出台的立案登记制司法解释,2017年去立案还是审查制,还一直试图让我主动放弃;二是感叹整个诉讼程序时间的漫长,真的特别耗人的心力……
于是,又翻出了三年前发过的一篇文章,虽然私下询问过不少医生和医学生,得到的答复都是“不会道歉”。还是希望,在缓和医患矛盾的过程中,可以换一个视角。
摘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马萨诸塞州通过第一个道歉法案开始,迄今美国已有35个州和华盛顿地区相继制定了道歉法案(I’m Sorry Law/ Apology Law),为了鼓励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主动认错,还在不同程度上排除了医师道歉在证据法上的自认效力。该制度实施后,不少州的医疗诉讼数量和医疗保险数额得到了下降。为了应对“医疗大走山”现象,缓和医患关系,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院2013年2013年7月23日推出《医疗纠纷处理及医疗事故补偿法(草案)》借鉴了此制度,该草案第6条规定“……依本章规定进行说明、沟通、提供协助或关怀服务过程中,医事人员或其代理人所为遗憾、道歉或相类似之陈述,不得采为相关诉讼之证据或裁判基础。”
当前,我国大陆地区医患矛盾也不断激化,医患双方缺乏相互信任。频繁出现的“医闹”、“暴力伤医”和“大处方现象”,与美国上世纪 70年代医疗过失诉讼中的“中彩”心态和“防御性医疗措施”极为相似。因此,医师道歉制度及相应的证据规则对于我国缓和医患矛盾,构筑和谐医患关系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医师道歉制度的发展历程
病人安全运动的社会背景
上个世纪,美国医疗侵权较侵权法的其他领域发展迅猛,给医患双方都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医师直接受到的影响是医疗过失保险率飞涨,一些高危医疗领域缺少专家和医疗服务。患者尤其是接受外科手术和产科服务的患者,则受到不断增加的防御性医疗的影响。美国医疗服务行业陷入重重危机。
1984年,一批不同学科的哈佛大学学者接受纽约州州政府委托,费时四年,耗费三百万美金,对当年全纽约州51家医院抽样取出的31,429份病历进行研究,因此该研究被称为“纽约研究”或“哈佛研究”。结果发现每100名住院病人中有3.7名受到医疗伤害,其中28%是医疗过失引起的;而在每8件可能成立的医疗伤害中,只有1件提起了诉讼。因此,该研究指出,当代医疗並非如大众所预期般的安全;相反,每天在医院所发生之医疗伤害事件件数並不逊于在高速公路上的意外事件。病人在法院所提出之医疗纠纷诉讼件数和庞大的医疗伤害件数相比,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至此,美国各界开始反思,发现医疗过失的问题事实上比医疗诉讼更迫切需要处理,对医疗纠纷解决的思维也从早期以提高病人诉讼难度为主的改革,逐渐转向以提升医疗品质、维护病人安全为主。在这一波病人安全的社会运动中,坦诚面对和公开错误,被认为是预防错误的关键因素。因此,各州都开始鼓励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公开、诚实地面对医疗过程中发生的错误,伴随着道歉的错误披露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
美国学者对患者起诉医师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患者及其家属遭受医疗损害时,除了有经济上赔偿的诉求外,其他非经济的诉求也同样重要,第一位的便是公开情况,追究真相,第二位是道歉,防止事件再次发生次之,最后是处罚等。并且,从心理学的视角而言,道歉代表着加害人承认自己是犯错者并且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因而加害人转换成苦恼的受害人;此种角色的转换,一方面可以平衡两方的地位,另一方面可以让被害人同情和同理加害人的苦恼,消除恶劣的情绪,从而引发原谅加害人的意愿。对于加害人而言,鼓足勇气面对错误及后续可能产生的责任,也有助于加害人减轻罪恶感获得自信。由此,道歉能够缓和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开展理性沟通、满足受害人的情感需求、促进和解,以及减少诉讼。
实际上,早在1981年,美国医学会就在其伦理准则中要求:“医师必须诚实并公开的告知病人所有医疗状况,病人有权利知道事实发生的经过,因为只有完全的披露,病人才能做出如何进行后续医疗的正确决定。”但是,在医疗损害纠纷的处理中,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认错和道歉几乎不可能发生。虽然发生医疗损害向病人表达歉意是医务人员伦理上的当然义务,但是医方不仅害怕患方会趁机要求巨额赔偿,也担心道歉和认错会成为法庭上对己方不利的证据。可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这一反应却往往激化了患者及其近亲属的愤怒,引发后续医疗诉讼等情况的出现;而这些又强化了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恐惧,更不可能向患者道歉,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因此,随着公开披露医疗错误的病人安全运动的广泛开展,作为促进医疗实务上公开医疗错误的重要机制,医师道歉制度开始以立法的形成出现。
美国医师道歉制度的沿革
全美第一个道歉法制定之初并不限于医师道歉,而是针对所有意外伤害的加害人。1986年,马萨诸塞州一个议员的女儿因车祸死亡,肇事司机从未向被害人家属表达过歉意。后来该议员间接了解到肇事者不道歉的原因,是担心道歉后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该议员决定推动立法为道歉者提供法律保护,鼓励意外事件的肇事者向受害人道歉,以弥补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心中的遗憾。不过,该法案仅保护表达同情的陈述,“向意外事故的受害人或其家属,就其因该事故造成的痛苦、死亡表达同情或一般性的关心等慰问的陈述、书面或致意的行为,不应该在民事程序中被当成自认责任的证据。”1999年,德克萨斯州制定了美国第二个道歉法案,同样只保护表达同情的陈述,对于包含承认过错的部分依然可以适用一般的证据法则。加利福尼亚州(2000年)和佛罗里达州(2001)年也沿用了上述规定。直到2003年,科罗拉多州才第一次将表达同情和承认过错的道歉都纳入法律的保护。
美国道歉法是各州分别制定的,是政策制定者所要追求的目标及各利益集团角力的结果,因此,在内容和效力上存在着差别。在制定道歉法的全部州中,30个州仅适用于医疗不良事件中的医师道歉,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马萨诸塞州、田纳西州、德克萨斯州和华盛顿地区的法律则适用于一切意外事件中的加害人道歉。更重要的是,各州立法在具体制度上,如道歉的内容、方式、时间限制、对象和适用程序方面也都有不同。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便出现了挑选法院(forum shopping)的现象。挑选法院是基于法律的不同,一方当事人从众多有管辖权的法院中选择一个最能满足自己诉讼请求的法院去起诉的行为。尽管挑选法院可能发生在侵权法的任何一个领域,但是医疗诉讼尤为脆弱,各州均已采取措施禁止诉讼发生在不同州的居民之间的挑选法院。另外,如果双方当事人试图将诉讼移交到联邦法院,挑选法院也会是一个考虑的因素。在伊犁州,挑选法院是不允许的,州立法管辖境内各类诉讼,除非有国会立法的存在。美国联邦证据法是1975年国会通过的,因此,联邦证据法通常管辖各类诉讼,而如果州法律被证明与权利密切相关或者是一项实质性州政策的,联邦法院只遵从州法律。在医疗诉讼中,如果一个州有完整的法律应对,联邦法院会遵循州法律来处理。但是,一个州是否有实质性的法律有时候并不清楚,便可能出现在医疗诉讼中当事人挑选法院到联邦水平,医师已经道歉,但是联邦证据法对此并不保护。因此,不少美国学者提出在联邦层面上建立对医师道歉的统一的保护。
实际上,美国确实也开始了对医师道歉制度联邦层面的改革。2005年,时任参议员的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提出的《国家医疗错误披露和补偿法案》,要求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数据库,强制披露信息,保护医师道歉不被用作医疗过失诉讼中的证据。不过,这项法案当时没有获得通过。另一个联邦层面的改革措施是安全港(Safe-Harbor)的立法,该法将保护医师不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如果他们遵循了实证医学的规范理论。例如,参议员罗恩•维登创建了对医疗过失可反驳的推定,如果医生遵循临床实践指南。这种方法的基本假设是医生没有过失,除非他们违反了公认的医疗协议,而该义务的违反符合侵权诉讼的标准构成要件。这种假设也塑造了一个基本命题:具体而言,对过错的一般承认不应该被作为医疗侵权责任的证据,因为这样的声明并不是对违反义务的指示。
美国的医师道歉制度
前文已述,虽然有小部分州的道歉法案并不特指医师道歉,不过,既然适用于所有意外 事故,医疗意外事件也当然包含其中。因此,在讨论具体内容时不再加以区分,而统称为医师道歉制度。
美国医师道歉制度的主要内容
各州的医师道歉制度在道歉的含义、形式、时间、对象和是否限于诉讼程序等方面,存在着差别。有些州只保护表示遗憾的语言,有些州则除此之外,还保护承认错误(mistake, error)、责任(liability)和过错(fault)。除了佛蒙特州仅保护口头的道歉,其他各州对形式没有明确限制,可以是口头、书面甚至动作,如送鲜花或卡片;多数州没有道歉的时限,不过,佛蒙特州只保护事故发生后30天内的道歉,而伊利诺伊州只保护72小时内作出的道歉,超出时限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虽然该规定是为了激励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早些道歉,但是,有些道歉其实晚些时候会更合适。大部分州规定接受道歉的对象必须是患者本人及其家属,而家属的范围包括血亲、拟制血亲、配偶及一亲等的姻亲(如继父、继母)。科罗拉州将亲属扩展到和受害人有家庭形式关系(Family-type Relationship)的第三人;康乃狄克州、乔治亚州、伊利诺州、路易斯安那州和缅因州将亲属扩展到患者的代理人或有医疗决定的人(包括监护人、律师或其他任何法律上认为有代理患者权限的人);有些州甚至包括患者或家庭的朋友,如德拉瓦州、爱德荷州和蒙大拿州;而夏威夷州、马里兰州、奥瑞冈州和佛蒙特州对接受道歉的对象则没有任何限制。道歉法适用的程序,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康乃狄克州、爱德荷州和蒙大拿州除了诉讼外还包括仲裁、调解等程序,路易斯安那州、维吉尼亚州、北达科他州和佛蒙特州更扩及行政程序,包含医师惩戒程序等。
在各州医师道歉制度诸多的区别中,道歉在内容上是否包含对错误的一般承认是该制度最关键的问题。主要表示同情、遗憾和慰问的道歉,被称为“部分道歉”(Partial Apology),而除此之外,还包括承认错误和责任的道歉,被称为“完全道歉”(Full Apology)。前者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代表,该州民事诉讼法第116(a)条规定:“对于因意外而受伤或死亡的受害人所承受的痛苦,向该受害人本人或其家属任何表达同情(Sympathy)或一般性致意(General Sense of Benevolence)的陈述(Statement)、书面(Writing)和动作(Gesture)均不能作为法庭证据使用。但若该陈述保护承认过错(Fault),则不适用此规则。”在立法理由中,立法者声称担心将承认错误的陈述也排除在法庭证据外会引发巨大争议,并提供实例说明表同情的陈述与承认错误的陈述的区别。如果在车祸发生后,肇事司机对受害人说“很抱歉你受伤了”或“很抱歉你的车坏了”,属于前者不能作为法庭证据;但是司机如果说“很抱歉你受伤了,这场车祸都是我的错”,或者“很抱歉你受伤了,我当时正在打手机没看到你过来”,就属于承认错误或暗示有错误的陈述,不能排除在证据之外。
完全道歉立法的州有科罗拉多、康乃狄克、亚利桑那、乔治亚、南卡罗你亚和佛蒙特州。一是因为患者及其家属想要了解对医疗损害发生的原因和经过,如果医务人员不愿意诚实面对,他们会因感到被背叛和不被尊重而愤怒,并为此提起诉讼;二是如果医务人员诚实告知有助于本身从罪恶感中解脱。第一个原因似乎与我国传统社会“讨说法”不谋而合,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借鉴该制度是必要和可行的。
美国医师道歉制度的反对声音
实际上,医师道歉制度在美国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开展。2001年美国医疗机构联合认证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f Accreditation of Health Organizations, JCAHO)将告知医疗过失列为医院认证的基本标准,要求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主动向患者或其家属告知所有非预期的医疗情况。但是,该标准公布后6个月,Rae M. Lamb的研究团队进行了全国性的实证调查,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医疗机构有医疗过失披露机制,二分之一正在制定相关的规定,其余则没有任何披露规定。医疗机构进行过失披露时,92%会包含解释、87%会进行事件调查、68%包含道歉,只有30%会承认错误和责任,36%愿意赔偿。另一项对548位医师和医学生对医疗过失披露态度的研究也指出,虽然高达97%的医务人员同意向患者告知轻微伤害的医疗过失,93%同意告知严重伤害的过失,但是发生医疗损害时,真正向患者告知的轻微伤害只有41%,严重伤害的更少,只有5%。
理论上,学者们都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有人提出部分道歉法保护的道歉,严格来说并不符合道歉的定义。因为心理学家或伦理学家认为,一个真正的道歉,是道歉者必须没有任何借口地承认其行为违反了规范并表示愧疚。欠缺该要件的道歉充其量只是同情、同理心的表示,并未带有不利自己的意思,本身就不是传闻法则的例外情况,没有必须特别立法保护。针对完全道歉,有学者认为此立法意味着道歉在法律的保护下,不再承担固有的法律风险,那么道歉在道德层次上的意义将被法律架空,变成空洞的语言而不具备让受害人原谅的力量。道歉法将使道歉成为和解的策略性工具。还有反对者从医疗文化出发,认为担心医疗诉讼并非真正阻碍医务人员道歉的因素。根据Kaldjian的实证研究,曾有医疗纠纷经历的医师不会因此倾向于不愿意披露过失,恰好相反,此种经历反而会增加披露过失的意愿。该研究结果和另一个加拿大医师及美国医师对于披露医疗过失态度的比较研究结果一致。
美国医师道歉制度的效果
尽管批评声不断,美国医师道歉制度实际应用后,确实在诉讼数量和赔偿额度上都有所改善。通过假设的理论,学者们不断从理论上解释医师道歉如何改变医患的相互作用。Bernard Virshup提出了一个服务模型,其中同情和积极倾听的结果是更有效的沟通和更少的诉讼。其他措施侧重于归因理论,认为道歉使患者不再将责任归因于个体医生,而是更广阔的系统性缺陷,从而缓和医患关系,减少医疗诉讼。
当然,道歉和披露错误制度成效的最好证据,不是精心制作的研究,而是鲜活的实证数据。最早也最经常被引用的是例子是,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的退伍军人事务医学中心建立的道歉和披露制度。经过一系列重大的医疗过失诉讼后,该中心实施了全面披露计划,患者将被告知给他们造成伤害的错误。披露之后,风险管理委员会会见每位患者确定帮助他们的方式,可以通过提供后续药物治疗或者赔偿。如果风险委员会确定医院的员工有过失,那个人将出席会议并向患者道歉。在1987年实施该制度后,医院报告和其他同类医院相比该院支付医疗损害赔偿数额达到最低四分位数,每项诉讼的责任到1996年也降到底部第六位。同样地,约翰斯·霍普金斯儿童中心的律师估计,从2001年制定了鼓励医生披露错误并道歉的正式政策起,诉讼的赔偿数额已经下降了30%,因为受害者和家人“欣赏(该院的)坦率和豪爽”。
密歇根大学医院的医疗损害纠纷,由风险管理小组和独立的卫生从业人员委员会(committee of independent health practitioners)审查。错误被透露给病人,如果一个不合理的医疗错误是伤害的原因,患者将得到迅速而公正的赔偿。这样一来,未决诉讼的数量减少了一半,每个官司的支出也有所减少,平均每年节约超过200万美元。同时,保险公司为了减少开支也开始实施披露过失的政策。COPIC,科罗拉州的医疗过失保险运营商,开发出了无过错系统,鼓励医生披露所有意想不到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不久作出回应,”并解决任何相关疑虑。这个程序实施后,医疗诉讼下降50%,结算成本下降23%。
从整体来看,实施医师道歉制度的州,不论是部分道歉还是完全道歉,相较于没有该制度的州,其医疗纠纷案件的和解效率都有提高,对重大的医疗损害案件(死亡或四肢瘫痪的),和解金额平均下降14-17%,而且,长期来看,医师道歉制度将可以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另有实证研究表明,有医师道歉制度的州,其医疗诉讼赔偿额平均下降3,2000美元,该制度对于产科、麻醉科和(或)婴儿有关的诉讼案件影响最大,赔偿金额也下降最多。因此,医师道歉制度确实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美国医师道歉制度对证据法的影响
尽管现有研究中,医师道歉和披露过错制度有很多益处,除了保护道歉的立法趋势不断增加之外,大多数被告的辩护律师仍然告诫医生不要向患者道歉。即使是那些建议道歉的专家们也非常谨慎地强调完整道歉内在的法律风险。而这些法律风险与美国的证据法上传闻证据排除和自认规则密切相关。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
根据联邦证据规则801(d)(2)的规定,允许将对方的承认作为证据,这意味着对方当事人在民事或刑事审判中做出的任何声明都不作为传闻证据被排除在外,即使该声明是在法庭外做出的。这条规则的理论基础为禁止反言,一方当事人自己的言论被认为是足够在法庭上反对他自己的。如果医生在审判中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失,根据规则804(b)(3),一个人做出的道歉将会被允许在法庭上作为反对自己的证据。此规则假定,将会引起本人民事或刑事责任的声明更可能是真实的,因此该声明比其他的庭外陈述更可靠。
有一些规则或许可以排除医师道歉的证据效力,但是十分有限。第一,第408条规定关于诉讼的妥协谈判中,言语不能被用作证据。因此,和解谈判过程中的道歉不被法庭所接受。这一规则背后的公共政策理由是,法院倾向于妥协和解决,并将保护谈判期间的声明,以鼓励双方之间的沟通。但是,道歉必须是在正式谈判中做出,因此,适用该规则前协议必须已经签订,并且诉讼必须取得进展。另外,根据该条规定,和解中的道歉仍然可以为了其他目的在法庭中使用,只要不用来证明侵权责任或抨击道歉者。例如,和解谈判中的可以在法庭上介绍,来证明证人的偏差或偏见,或者否定一个无理由拖延的争论。
第二,第403条有时候也被提出来,因为该规则禁止这样的证据,当它的作证价值基本上被不公平的偏见、误导陪审团的危险抵消时。但是,这一策略并没有见到成功,法庭可能认为医师的道歉没有不公平的偏见,而且具有高度的证明力,“因为它揭示了医疗专家对自己行为的评估,该评估与违反诊疗标准问题和具体过失的认定有关。”
第三,第407条和409条。前者规定不得将事后补救措施的开展作为证据,后者则排除医疗机构提供和支付医疗费用的证据效力。不过,这两条并未涉及道歉。根据目前的制度,过失造成患者损害的医师可以采取措施来防止错误再次发生,甚至可以支付未来的医疗费用,而无需承担法律风险,但是道歉不能避免此风险。
判例中的医师道歉
在各州道歉法立法之前,早期的案例中便有因为上诉法院发现医师对“错误操作”和“误操作”的承认不足以证明责任,而使得原审判决逆转的情况。在1924年Markart 诉Zeimer案中,被告是原告的疝外科医生,因为手术的错误原告失去了他的右睾丸。医生坦率地承认了错误,并且有人告诉原告的朋友“原告的手术有过失”。原告依靠这种说法来证明医师的责任,并未提供专家证词。法院认为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这种承认不是“对过失的承认,也不是对缺乏开展该手术所需的一般技能的承认”。法院认为,“这一错误的操作在实施当时可能被认为是正确的。”
目前,医师道歉是否作为证据被采信,各州仍有所不同。在加利福尼亚州、康乃狄克州和奥克荷马州的一些案例中,法院认为被告医师的道歉会发生自认过失的法律效果,可以作为审判外的过失自认。乔治亚州和佛蒙特州的高等法院则认为,道歉本身不足以证明医疗诊疗标准,也不能充分地证明过失。如在Phinney诉Vinson案中,医师向患者道歉承认其医疗程序不当,患者主张医师的道歉足以构成赔偿责任的自认,不过,佛蒙特州法院认为该医师认错的道歉并不足以认定医师已构成赔偿责任。
修改联邦证据法的主张
尽管医疗过失(Medical Malpractice)是州侵权法,但是大多数州在保护医师道歉方面存在不足。由于联邦证据规则影响许多州的证据法,通过联邦证据规则保护医生的道歉,将为各州提供一个可遵循的清晰模式。事实上,如果让各个州进行修订,不仅费时,而且效率很低,因为毕竟现在只有8个州实行保护医师完全道歉制度。这样的改变将减少语法上的混乱,安抚那些担心道歉的风险被用来对付他们的客户、可能在随后医疗事故诉讼导致对自己不利的律师。
当然,修订的主张上学者们意见也不尽相同。有学者建议调整第408条,将现行法保护诉讼之后的和解谈判中的道歉扩展到诉讼之前。对此,有学者认为,第408条的目的就是在诉讼已经存在后保护和解谈判,法院已经建立了判例法,以确定妥协的谈判是否在进行中。而且这种扩展太过激进,加入新的规则将是个重大的、不可能的举动。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认为修订第409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该条原来的文本已经集中在医疗伤害及改善他们的努力措施上,而且规则本身相对较短和简单的,不像第408条的语言那么复杂。建议将第409条规定的“提供或支付或承诺支付医疗、住院或发生在损害中的类似费用的证据,不被认可证明人身伤害的责任”,修改为“1.提供或支付或许诺支付医疗、住院或发生在损害中类似费用的证据,不被认可证明人身伤害责任。2.医疗专业人员作了道歉或一般性承认错误的证据,不被认可证明人身伤害的责任。”该建议将道歉的保护限制在了医疗专业人员所做的声明。尽管在任何侵权发生后道歉都是合适的,但是缺乏对医务人员道歉的保护对整个社会尤其有害。医师未能披露错误并道歉不仅涉及大量的医疗事故索赔诉讼和保险费率的提高,而且导致公众对医疗领域整体的不信任。另外,如果医疗过失不被承认和披露,将难以解决和避免再次发生。最后,仅仅在医疗过失侵权领域中,出现了受害人想要道歉和解释超过经济赔偿的现象。因此,在修正案中明确提出医疗专业人员做出的道歉比对所有侵权行为中加害人的道歉更为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保护全面道歉甚至对过错一般的承认,和医师道歉后不再承担侵权责任是不一样的。如果有医师道歉以外的其他证据证明该医师违反了诊疗标准,他仍然要面临潜在的法律责任。正如科恩指出,“当一个人的过失很容易通过道歉之外其他独立的证据证明,在道歉的时候承认过错对原告的证明能力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建议的修正案将起到区分只存在独立确凿证据的诉讼和那些唯一证据是医师自认的诉讼。前者可以继续审判或和解,而后者可能因证据不足而驳回。乍一看,这对于医疗过失诉讼中既没有证人,除了医师道歉外没有其他证据的受害人来说,似乎很残酷。实际上,这名受害人在现行法下可能处在相同的情况,因为如果承认错误及责任的道歉将决定审判的结果,那么,为了规避风险医师是不可能道歉的。
结语
从美国医师道歉制度的发展来看,该国医疗纠纷解决制度已经进入以承认错误为出发点的成熟期,也就是说,既然医疗纠纷的中上游是那个根本的医疗过失问题,解决医疗纠纷正本清源之道,应该是积极的寻求减少医疗过失,让医疗损害不再发生,而非着眼于提高病人提出医疗纠纷诉讼之障碍。而且,医疗损害发生后,患者常常非死即伤,家属或者患者本身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难免会带有种种情绪,并指责医师,而造成医师感到沮丧、不信任和灰心;医师道歉制度可以还原医师在伦理上“病人捍卫者的角色”,促使因医疗纠纷而紧绷的医患关系由对立走向和谐。
不过,美国医师道歉制度的专门立法,是为了处理在证据法则中,被告医师审判外供述的证据是否适用传闻法则。根据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73条之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因此,我国民事诉讼中尚未确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而医师道歉是否产生自认的法律效力,我国也仅在司法解释中有所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第1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当事人无需举证”,在我国法律文件中首次确认了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比较全面、准确地规定了自认制度,但仅限于在诉讼过程中的自认,且没有采用“自认”的称谓,而以“当事人承认”来表述。
诉讼外的自认,虽然不具有诉讼法上自认的效力,但仍然具有间接事实的性质,作为当事人举证证明己方事实主张的一项证据,由法院自由审查判断其证明力。因此,完整的医师道歉在我国现行制度中,虽然没有自认的效力,仍然具有证据的能力。实务上进行医疗纠纷调解时,医师有无道歉也是抚慰患者及其家属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借鉴美国医师道歉制度的规定及证据法的修订意见,明文排除诉讼外医师道歉的证据能力,让医师在法律风险免除下敢于道歉和披露过失,从而避免医疗矛盾的恶化,实现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本文发表在《证据科学》2014年第6期
- 本文授權資料來源:医药健康报告
王丽莎
-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北京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卫生法学理事、中国医师协会医学人文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本科曾学习临床医学,从事医学法学交叉学科理论、实务工作11年。
- 电话/微信:15120007769
- 邮箱:liza52534@126.com
- 《人工智慧基本法》三讀通過,醫療責任如何界定? 1/14
- 中草藥安全別輕忽:天然之下的法律風險 1/2
- AI醫療的倫理規範與責任釐清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