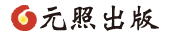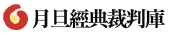自由選擇的死亡與適切的死亡──談荷蘭失智婦人的死亡意念與法律判決(醫學人文品評)
文章發表:2022/06/20
「我不想活了,但我並不想死。」若說這句話就是法律目前在生死抉擇上的難解困境─非生即死,那麼,醫療照顧恰好為此提供了不同的答案。生死這件事在法律概念上被簡單的化約,但在醫療照顧上,被賦予血肉與靈魂的聲音:「我若無法再以我所希冀的樣態活著,那麼請協助我適切地迎接死亡。」此時,生死便相接在一起,而非對立,並非選擇死就代表剝奪生。
一直以來,法律相當慎重的對待生命權,卻鮮少傾聽這些被捍衛著的生命,或該稱「尚有一息的狀態」,是否真以他所想要的姿態活著。但若我們承認,某種活著的狀態是否還堪忍受只有當事人可以決定,便又將重擔全壓在了病人身上,彷彿只有由病人口中得到了意願表示,才能開啟下一步的所有行動,這個意願表示是個釋放所有人的金鑰,一旦當事人不願表達、帶有遲疑或甚至是不能表達,就再也沒有人能夠開啟這道鎖,於是個人的意願表示就成了一把只能親自打造,而不容許被模擬鎔鑄的金鑰。個人的意念對於主宰自己生命中的所有事務效力強大,然而我們卻時常忽略了,意念本身不一定精確,甚至,意念中的一切未必最適切。
也許少有人質疑過,自由選擇的死亡是否就是最適切的死亡?這個乍看之下毫無疑問的假設,事實上破綻百出。適切的死亡不一定符合病人最真實的意志,但可能是當下生命及關係連結狀態的最好選擇;而自由意志選擇的死亡,卻不一定是當下生命及關係連結狀態最適切的選擇。
上述這些概念正好建構了荷蘭於2019年眾所矚目的一起終局判決─2014年失智婦人執行安樂死的爭議案件,相當重要的起訴與判決核心。這位失智婦人在尚有心智能力時預先簽署了同意安樂死的文件,表明一旦自己生活需要仰賴他人並住進護理之家時,便希望執行安樂死。爾後病情進展,婦人連鏡中的自己都不認識,醫師評估後認為符合執行安樂死文件中的意願,便將鎮靜藥物添加於咖啡中讓婦人飲下,後因婦人再度清醒,失智婦人清醒後似乎對於當下的情況顯得抗拒,便在家屬壓制下由醫師施打致命的藥劑,迅速地結束其生命,遂其安樂死意願。
然而,檢察官起訴了醫師,認為他在婦人抗拒下執行安樂死藥物的注射,是違反意願的置人於死,相當於謀殺。而最後法官所給的答案是:「醫師已踐行安樂死法規所規範的程序,我們看不出這位醫師有任何違法之處。」同時也表示:「一個連自己都認不得的人,顯然無法在當時對醫師再次表達自己的意願。」法官並沒有正面回答檢察官的問題,而是針對當時的處境進行了客觀的判斷:確實無法再次確認婦人的意願,因此以婦人之前所簽署的安樂死意願作為是其真正的想法,醫師已經完整實踐了安樂死相關法律規範的程序。
檢察官想要知道的是:「萬一她不想進行安樂死了呢?」法官回答:「無從在當下再次確認,所以尊重先前表達過的明確意願。」是的,一直都是「意願」的難題。如果因為無法再次確認就不能執行,那麼人們只好在自己不願意苟活的狀態下殘喘;如果因為無法再次確認就執意執行,那麼人們又失去了隨時可以改變其意志的自由。但若失去決定能力是大多數失智病人的最終樣貌,我們勢必得面對以下的幾個問題:.....
全文刊登於月旦醫事法報告,第39期:菸品管制與公衛政策 訂閱優惠
- 《人工智慧基本法》三讀通過,醫療責任如何界定? 1/14
- 中草藥安全別輕忽:天然之下的法律風險 1/2
- AI醫療的倫理規範與責任釐清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