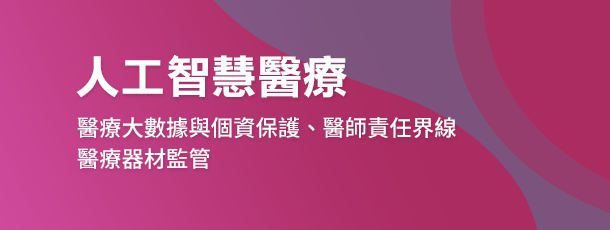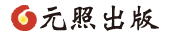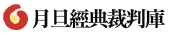憑權利和約定贏得尊嚴
文章發表:2017/03/24
胡晓翔
--卫生与健康权利保障的法律体系建构,从《侵权责任法》施行谈起--
人在自然能力上不平等,但凭着权利和约定而成为平等。人最基本的平等,在于生存权的平等,健康权是生存权最核心的部分。这些“约定”,就是卫生与健康保障法律体系,它应使得自然能力千差万别的社会成员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保障权利,赢得最基本的人格尊严,这是社会最基本的生命伦理底线。《侵权责任法》试图建立一元化结构的医疗损害责任制度,引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条例》)的存废之争。作者认为,围绕医患纠纷的民事赔偿法律规制,今后绝不会归于“一元化”,而是继续保持甚至愈加“多元化”的态势。《侵权责任法》与《条例》肯定将并行不悖、各有侧重与分工。除《条例》将继续发挥规制作用外,对于《侵权责任法》生效之前诊疗行为结束并已出现损害后果的案例,事发当时有效的其他含有侵权责任规定的法律可能被优先适用。也不能利用“法律适用规则”以《侵权责任法》代替《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宪法》以及有关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为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及其拓展性文件规定了庞杂的“健康权”相关内容,亦不排除被优先于《侵权责任法》适用的可能性。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权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保障社会权最有效的方式,具体的举措就是颁行《基本医疗卫生法》。
Men are unequal regarding natural ability, however, men become equal by virtue of promises and rights. The most fundamental human equality lies in the equal right to live while the health right is the core of it. These promises are the legal systems of sanitation security, which shall enable social members who differ tremendously in natural abilities to enjoy equal right of basic medical care and to win the most fundamental personal dignity, and that is the bottom line of society concerning life and ethics. Tort Liability Law tries to build a centralized liability system for medical damage, which caused the debate on existence or abolishment of Regulations on the Handling Medical Acciden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Regulation).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laws & regulations of civil compensation targeting medical dispute shall be keeping diversified other than being centralized. Surely, the Tort Liability Law and the Regulation will not conflict while they focus differently and work with joint effort. Except for the cases where the Regulation keeps functioning for stipulation, “law application rule” may not be quoted to replace General Rules of Civil Law with Tort Liability Law even though other valid laws that cover tort liability may have been applied with priority for the cases the diagnosis & treatment is completed and the damage occurs before Tort Liability Law comes into effect. The complicated health right is stipul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Article 12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nd its extension documents, where the possibility of application prior to Tort Liability Law is not excluded. To realize the social rights via justice is the compelling obliga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secure the social rights, to be specific, here we talk about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asic Medical Care and Health.
生命和自由决定了人,是人获得自然权利的依据,社会必须建立在普遍地承认人的生命、自由、平等的基础上。人在自然能力上不平等,但凭着权利和约定而成为平等。[1]《发展权利宣言》(联合国大会1986年12月4日通过)第八条第一项要求“各国应在国家一级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发展权利,并确保除其他事项外所有人在获得基本资源、教育、保健服务、粮食、住房、就业、收入公平分配等方面机会均等。…”人最基本的平等,在于生存权的平等,健康权是生存权最核心的部分。生存权及健康权是“天赋人权”,且属于积极人权,这就为个体向社会、政府和国家要求保护和保障具有了天然的正当性。不过,仅有这些“权利”的体认与倡导,是不够的,还须有强制性的“约定”,这些“约定”,就是卫生与健康保障法律体系,它应使得自然能力千差万别的社会成员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保障权利,赢得基本的人格尊严,这是社会最基础的生命伦理底线。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于2016年8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这段尊重卫生与健康行业本身固有规律的话背后,体现的伦理逻辑,可见201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记者彭波采访清华大学法学院原院长王晨光教授的《卫生立法应凝聚社会共识》一文,该文阐述道,“健康权属于‘积极人权’,需要通过政府、社会、其他组织和专业人员的帮助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实现”。
如何落实习总书记的指示,笔者领会有两点认识。
一个是强化了行政作为的责任,即,“我们将迎难而上,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探索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式解决办法”,这一实质性医改是强化行政作为、履行公权职责为主心骨的改革。再一个是实质性医改必须体现为以《基本医疗卫生法》为统领的全面的医改规制,依法医改,是政府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必然途径。所以,本次卫生与健康大会是真正敲响了“医改市场派”的丧钟。
另外,我们必须尊重纳税人对于公共产品的请求权,比如对于卫生医疗体系的请求权。有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之前,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支出和社会支出占80%以上,患者自付部分低于20%。2002年,政府和社会低于41%,而患者支付高于60%。而发达国家居民自负卫生费用平均为27%,转型国家为30%,发展中国家为42.8%。从2008年开始,政府开始重视医疗费用的合理化,这与纳税人以及纳税人的代言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2]
谈到卫生与健康保障法律体系,我们不得不首先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该法于2010年7月1日起生效施行。其第七章专章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试图建立一个一元化结构的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改变二元化结构医疗损害责任的法律适用矛盾状况。[3]杨立新教授认为,在《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前的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是由三个双轨制构成的二元化医疗事故与医疗过错救济体制。三个双轨制的内涵是:一是医疗损害责任诉因的双轨制,既有医疗事故责任,又有医疗过错责任。二是医疗损害赔偿标准的双轨制,医疗事故责任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赔偿,医疗过错责任适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三是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的双轨制。[4]杨教授“三个双轨制”说,其实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存废之争。
1 《侵权责任法》与《条例》的关系问题。
《南方周末》2010年8月19日第八版刊登的《实施8年争议重重,与侵权责任法冲突明显,法律专家呼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当休矣》一文,可谓集“废《条例》论”派观点之大成,引起很大反响。该文的主要观点是,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由于对“医疗损害”作出了专门规定,医疗诉讼中将不再有“医疗事故”的提法,被诟病多年的《条例》再无涉足医疗诉讼的理由。文章说法学界在此问题上近乎达成共识,并转述烟台大学郭明瑞教授的看法云“侵权责任法最大的贡献,就是废除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
在《侵权责任法》生效之前,确实有很多法学权威、卫生管理领域的官员认为,一旦《侵权责任法》施行,《条例》自然就废止了。至于“法学界近乎达成共识”云云,实是闻所未闻的一家之言。实际上,从基本法理层面来分析,很明显,我们只能得出《侵权责任法》与《条例》肯定并行不悖、各有侧重与分工的“预测”[5]。事实上,2010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生效施行后迄今的实际情形也确实如此。权利保护规范的多元化应该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常态,是政治昌明、法律发达的结果,我们理应理解、习惯。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会知道,围绕医患纷争的民事赔偿法律规制,本来岂止是“二元化”,今后也绝不会归于“一元化”,而是继续保持甚至愈加“多元化”的态势。
1.1 尽管《侵权责任法》就“医疗损害责任”做了专章规定,但是,无法取代《条例》,有两方面的理由。
1.1.1 首先,两者的“法域”不重叠。
《条例》围绕“医疗事故(医疗纠纷)”的预防、处置、鉴定、处理与监督、赔偿、处罚等整个流程,全方位地设计规范,是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的混合规制,尤其是预防、报告、接待、处理、鉴定、行政处罚等内容,其他法律法规无可替代,《侵权责任法》更是“未着一字”,何来替代之说。
1.1.2 其次,《条例》关于医疗事故损害民事赔偿的一章共七条规定,不但继续合法有效,也是具有可操作性之便利的。
在《条例》的存废之争中,“废止派”还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观点:即便《条例》作为完整的一部行政法规没有被废止,但是,其第五章专门规定了《医疗事故的赔偿》,尤其是其中的第五十条直接规定了民事赔偿的具体操作性内容,与《侵权责任法》有所差异,应该单章或单条作废。如梁慧星教授就认为:“本法一经生效,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关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的规定将同时失效,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责任案件,应当适用本法第七章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而不再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6]。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条例》关于医疗事故损害民事赔偿的一章共七条规定,不但继续合法有效,也是具有可操作性之便利的。
《条例》规范的“医疗事故”是“医疗损害”的形式之一,“医疗损害”是个集合的概念,“医疗事故”是其子集。《条例》的“医疗事故”概念及其赔偿规范,仅仅针对民事权利的绝对权中的生命权、健康权的损害。其合法性,渊源于《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
《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
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
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立法法》第五十六条规定:
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
(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行政机关依据法律颁布行政命令和行政法规,是“授权立法”行为。[7]立法权来源于授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法规中的法条授权的授权立法是一般授权立法。
新《立法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本款规定,实际上肯定了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的效力比国务院非经授权制定的一般法规效力高。[8]更进一步,学界认为,依据本款的规定,可以得出结论:法律与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具有相同位阶。[9]《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无精神损害赔偿,也无具体的赔偿项目和标准,不具有操作性。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1987年6月29日)、《条例》(2002年9月1日)均围绕“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而对医疗事故的赔偿依法依据法律的创制性规定作出具体化的规制,并没有侵犯法律的专属立法权,完全合法。且,与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法释》(2001)第7号(2001年3月8日)的规范保持了内在的协调性,又突出了医疗卫生行业的特殊性,就此部分而言,可谓既合法又合理的“良法”。[10]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也可以在《条例》里得到具体体现。很多权威专家并没有搞清“死亡赔偿金”的确切内涵、时代背景及其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关系,而抨击《条例》的有关规定,就显得无的放矢。
2010年7月21日《健康报》的《卫生与法》版刊有著名卫生法学专家陈志华的《正确理解新旧法之异同》的“侵权责任法导读文章”,第三自然段说“《条例》没有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他的这个看法,与广东省廖新波的看法基本一致。“医生哥波子”(廖新波副厅长的网名)在2010年3月31日的博文《<侵权责任法>挑战低成本运作——学习《侵权责任法》体会》中说到:
四、 构成医疗事故不赔偿死亡赔偿金的规定将寿终正寝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患者死亡是没有死亡赔偿金的,因此扣除医疗费用外,对死亡患者的赔偿很难超过20万;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应当要赔偿死亡赔偿金,按照广东省一般地区的2008年标准,单此一项的赔偿就达到40万左右。
此观点的更早渊源在2010年1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一书:“《条例》未规定死亡赔偿金,…因而在医疗侵权造成患者死亡的情况下,按照医疗事故适用《条例》所得到的赔偿将明显少于按非医疗事故适用《民法通则》和司法解释所得到的赔偿。”[11]
这些说法,都不恰切。
民事侵权损害的精神赔偿问题,最早的文字规范,出现于《法释》【200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此解释于2001年2月2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1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其第九条细化规定:
第九条 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
(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
(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
(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
因此,其后于2002年9月1日生效施行的《条例》第五十条细化规范的十一个赔偿项目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项,就其立法本意来说,是在医疗事故赔偿领域嗣轨、具化《法释》【200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精神,在死亡案例里就是“死亡赔偿金”,在其他事故案例里就是“残疾赔偿金”。《条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具有很强的操作便利性。
对《条例》的这个误读,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许多法学权威都持此说,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12]
2 《侵权责任法》与《民法通则》的关系问题。
在《侵权责任法》的宣讲中,有很多权威认为,中国自2010年7月1日开始终于有侵权责任法律规制了。其实,《民法通则》第六章第一节第一百零六条的第二、三两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三节从第一百一十七条至一百三十三条,共用十九个条款规定了“侵权的民事责任”。那么,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一般认为,很简单,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也是新法与旧法的关系,一旦有差异,毫无疑问,适用《侵权责任法》。
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民法通则》为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基本法律,而《侵权责任法》系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法律,两者并非“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不能依据新《立法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得出“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的结论。
尽管《宪法》和《立法法》没有明确规定基本法律的位阶高于非基本法律,但从《宪法》和《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中,还是可以得出这一结论。此外,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正当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的正当性,一定程度上是不同的。基本法律的正当性要高于非基本法律,其法律位阶也应高于非基本法律。[13]亦即,《侵权责任法》并不能利用“法律适用规则”来代替《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
3 “归于一元”抑或“愈加多元”。
法学界权威们对《侵权责任法》的主要期待之一,就是所谓的“二元归一”,即,以为“创造性地”设计了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的专章规定,今后“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的,统一适用本法的各项规定,从而有利于消除二元化现象。”[14]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可知,“归于一元”之虚妄。岂止如此,实际上,关乎医事活动中多方主体的作用及利益需求的法律规制,只会“愈加多元”。
3.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
2010年6月3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其第一、第二两点内容是:
一、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
二、侵权行为发生在侵权责任法施行前,但损害后果出现在侵权责任法施行后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这也就明白无误地决定了,2010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生效施行之后,涉及医疗损害赔偿纷争的民事诉讼案件的法律适用,是《侵权责任法》这“一元”,与“当时的法律规定”并存的。而“当时的法律规定”本身就是多元的,因此,不可能“归于一元”。
3.2 《侵权责任法》第5条的规定。
再者,《侵权责任法》第五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据本条规定,本法与其他含有侵权责任规定的法律,构成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人民法院应当优先适用特别法关于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定。[15]即便我们把“其他法律”严格限定于“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包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也至少还有《献血法》、《执业医师法》、《传染病防治法》、《药品管理法》、《食品安全法》、《母婴保健法》、《红十字会法》、《国境卫生检疫法》、《职业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产品质量法》、《国家赔偿法》等等法律可能被优先适用。
3.3 除此而外,还可能有国际公约被优先于《侵权责任法》适用。
根据国际法上的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对于一个国家签署或加入的国际条约,除非做出保留等,一般即在该国发生效力,国家有义务使其国内法与依国际法承担的义务相一致。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法高于国内法规则,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的法制实践所接受。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凡是全国人大决定批准的条约和协定均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具有同等的地位和效力。[16]中国政府先后于1997年10月、1998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作出了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
3.3.1 该公约第十二条及其拓展性文件规定了庞杂的“健康权”相关内容。[17]
该公约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
此款应当注意的是,对健康权的提法上,公约用了“最高”(英文highest)这一副词,这是其他社会权利所没有的。这就是说,公约在健康权方面,对缔约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需要缔约国在此方面运用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力量尽最大努力实现之。这是因为,于人而言,健康权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没有了健康,公民的生活质量就大为降低,何谈享有其他权利?[18]
国际社会对缔约国贯彻国际人权标准进行监督,是《经社文公约》所包含的一项重要机制。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被授权监督《经社文公约》的实施情况。[19]不排除,我国公民依据其提起诉讼的可能性
3.3.2 不容忽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2008年12月10日,联合国第63届大会决议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有很多国家签署了这一议定书,中国也面临着签署该议定书的国际压力。[20]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第二条 来文
来文可以由声称因一缔约国侵犯《公约》所规定的任何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受到伤害的该缔约国管辖下的个人自行或联名提交或以其名义提交。
第六条
二、收文缔约国应当在六个月内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解释或陈述,澄清有关事项及该缔约国可能已提供的任何补救办法。[21]
这就表明,在国内社会权利保护措施不足的情况下,该议定书允许个人和群体到联合国经社文委员会寻求国际救济。[22]
增强社会权利的可诉性,实现社会权保护的司法化,是社会权利保护国际化的迫切要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个人和群体在到联合国经社文委员会寻求国际救济前,需要用尽国内救济。如果我们国内只有行政救济程序而没有司法救济程序,公民就可直接向联合国经社文委员会申请救济,对国家的压力是很大的。[23]
3.3.3 在社会权利的保护上,我们国内当下可能确实只有行政救济程序而没有司法救济程序。
公民的社会权利,以及国家的责任,除已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外,只在《宪法》里有比较简洁的表述。有关医疗卫生及健康保障的,如下。
《宪法》第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
第三十三条第三款: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第四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在司法化的层面,民生保障领域具化立法不足,尤其是健康权保障方面,迄今并无一部规制性母法用于明确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和公民的义务与权利,和用于司法救济。而早在一九五五年,最高法院曾就法院在判决中可否援引宪法问题作过一个司法解释,不同意在审判中直接引用宪法条文,各级法院至今还在遵循这个原则。[2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已成为世界性的一项宪政惯例,而我国宪法基本权利尚无直接效力,即公民不能依据基本权利提起诉讼,所以,国家机关履行义务的动力不足,进而导致基本权利实际上只是国家的“恩惠”[25]。在我国实现宪法基本权利直接效力之前,推动宪法基本权利法律化(如在《医师法》中明确“待遇、教育”等等方面的权利规定),使基本权利经立法后取得司法效力,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真正有法律上的保障。
而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和公民的义务与权利不明确的话,新的《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项确立的行政给付诉讼制度也会是无源之水,没法实质启动。因此,要切实落实本次卫生与健康会议精神,可靠推进实质性医改,我国亟待出台规制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和公民的健康义务与权利,和用于健康权司法救济的基本医疗卫生母法。
3.3.4 关于《基本医疗卫生法》立法的思考。
中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合法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权利能否得到有效保障。[26]
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由此出现“生存风险”,这就给政府出面主导克服经济的低效率、调节再分配、安排人们消费“维护自身最佳利益”的“有益物品”提供了现实依据。市场失灵引致的典型的“生存风险”主要表现为:
其一,市场的趋利性导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短缺。除非于己有利,着眼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显然不是理性经济人愿意提供的。政府对此作出回应的有效措施就是主导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其二,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贫富分化和难以接受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通过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策略有助于缓解差距过大的矛盾。[27]而通过司法实现这些社会权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保障社会权最有效的方式。[28]因此,出台《基本医疗卫生法》直接的便利之处就是服务于司法层面的救济。
2014年12月30日上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基本医疗卫生法起草工作机构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基本医疗卫生法起草工作启动仪式,标志着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负责牵头起草的、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基本医疗卫生法》的立法工作全面启动。《基本医疗卫生法》立法,是当下的热门显学,论文多,课题也很多。关注度高,是好事。但还不够,可能还需要有些理性的理论准备。需关注的要素很多,仅谈其中一个。
新华社北京2016年8月26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6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坚持预防为主,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调整优化健康服务体系。要坚持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坚持政府主导。要强化组织实施,加大政府投入。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抓紧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坚持问题导向,抓紧补齐短板,不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坚持政府主导”,这就明确了,医改的大方向是进一步强化行政作为的力度,履行政府职责,彰显执政党胸怀。也就给作为医改总蓝图的《基本医疗卫生法》立法指明了准则和思路。
本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把握好一些重大问题。要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不断完善制度、扩展服务、提高质量,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要坚持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让全体人民公平获得。要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要有所为,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市场要有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到了啃硬骨头的攻坚期。要加快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任务落到实处。要着力发挥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性,从提升薪酬待遇、发展空间、执业环境、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身心健康,通过多种形式增强医务人员职业荣誉感,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风气。
总书记的强调,显然给我们的医改,给医改的“总蓝图”----《基本医疗法》立法工作,指明的准则和思路,我理解,可以明确两点:
一,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发展目标是全民免费享有。
二,公立医院的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国家保障性行政法律关系。
3.3.5 “公民免费享有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是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的必选举措。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说明,“建议通过后,还要根据建议制定‘十三五’规划纲要。建议重点是确立发现理念,明确发展的方向、思路、重点任务、重大举措,而一些具体的工作部署则留给纲要去规定。”
笔者以为,“公民免费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医疗卫生服务领域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的必选举措,在制定“十三五卫生规划纲要”时,必须围绕此举措构建十三五发展蓝图,以此与《基本医疗卫生法》的立法工作相呼应。
理由如下。
一,这是中共中央早先“‘十三五’规划建议”的应有之义。
我们来看,《建议》明确的“‘十三五’时期我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假如还需要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筹措经费、劳神费力,这样的人民是谈不上“主体地位”的,他也体会不到他是“发展的中心”。由于单个家庭、个人的支付能力的巨大差异,付费才能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话,他的“平等发展权利”也就无从保障了。
《建议》提出的“‘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是,“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人民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靠支付能力迥异的家庭,个人购买的服务,就不可能有“均等化”。因此,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的含义,就是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免费享有模式。这恰恰与《建议》阐明的“完善发展理念”相一致:“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免费享有,由政府财政及社会筹资渠道“买单”个人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支付的部分,这才是“共享理念”的体现,可以使得“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这是一份最刻骨铭心的获得感!也是实现人民“免于匮乏的恐惧”权利的最切实手段!
二,这是《宪法》赋予政府的责任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宪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保护人民健康”。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还需要自费购买,就不能体现国家是如何有效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是如何公平、可及、均等化地保护人民健康的。
《宪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针对健康权这个积极人权而言,显然不是说“自费购买”,而是“免费共享”、依规分享,甚至是经由行政给付之诉而获得。
三,这不是一件很难承受的举措。
日前发布的《2014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4年全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35378.9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支出10590.7亿元,占29.9%;社会卫生支出13042.9亿元,占36.9%;个人卫生支出11745.3亿元,占33.2%。卫生总费用占GDP百分比为5.56%。
“个人卫生支出11745.3亿元,占33.2%”,可见,实际上,“公民免费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相当大程度上已经实现。政府财政和社会筹资渠道只要再进一步,把这一万多亿中的比例不大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部分承担下来,就是不折不扣地实现“全民免费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了!同时,对公立医院进一步控费,推进分级分工医疗,调整公立大医院规模,可以大幅减省财政投入。即,经过综合医改,完全可能在政府财政负担并不明显加重的前提下实现全民免费基本医疗。
综上所述,笔者呼吁,国家有关部门要准确领会《建议》精神实质,在制定“‘十三五’规划纲要”时提前布局,更要在正在制定的《基本医疗卫生法》中明确宣示“我国要在‘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深化医改,实现全民免费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制度”。
3.3.6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该问题理当是卫生法学这个学科最基础的课题,也应该是国家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保障法立法的最基础课题。但是,如此重要的根基性问题,却被学界轻忽多年。
笔者以为,从立法技术来理解,要立一部法,假如,我这部法即将规制的社会有关主体,事务,社会关系等,它们的法律属性问题不先行讨论,并在某个位点求得各界最大公约数的话,这部法,立法条件就完全不具备啦。2014年10月26日,在一个海峡两岸卫生法学术会议上,发的材料中有一册专著,《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我国基本医疗卫生立法研究》,汪建荣著,法律出版社,名人名社,但浏览一过,没找到针对性的阐述。其《居民最低医疗保障制度的性质》一个小节五行字,其实没说医疗保障制度的性质。而会议的论文集收的台湾学者陈俞沛的文章,里面的《社会保险之性质与特色》一个页面,人家就明确说“社会保险属公法关系”。论文集另一篇论文,《刍议基本医疗卫生立法需要构建的卫生法律制度》,作者张华,达庆东,程得广,也未涉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达庆东教授可是卫生法学界的老把式啦!就我目力所及,其他的一些专家教授有关此题的专著、专论,也大致这样,罕见针对性的明确阐述。具体观点可以讨论、争鸣,但不可缺如。目前,大陆地区的基本医疗卫生法立法研究,基本如此,就是说,核心问题,尙未及研究,笔者在2001年11月出版的拙著《冷眼观潮--卫生法学争鸣问题探究》里集中一章,专门论述“国家主体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在法定职责内形成的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问题。之所以执着于这个话题,自然是因为它太重要,不研究好它,不仅是《基本医疗卫生法》立法无门,而且,关乎八成以上的医疗卫生服务的法律规制,都会迷途。
二十多年前,本人挑起“争端”呼吁研究这个问题时,学界或讶异,或鄙夷--这是问题么?大家共识,就是且只能是民事法律关系!这个法律定位,对于主要提供国家保障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立医院的医患关系来讲,显然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的。这“一律民事说”的影响,至今依然强大,还是正式出版的几百种卫生法学专著、教材的主导观点。
与此相左的,另有俩看法,当年都是“独孤派”,即,几乎仅为看法提出者个人一人的看法。
笔者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始建构“国家主体医疗卫生事业中法定业务领域的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法律关系,其侵权损害赔偿适用国家赔偿法律”的观点,以十多篇长文论述,基本得以确立。尽管法学界和卫生法学界一片否定声,但迄今未见有学理分析细致到位、论证扎实的文字。
否定的理由,主要俩。
一,医院不是行政机关,它不可能有行政权力,怎么能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这是固步自封于旧的行政法学理论,没有及时更新知识,不知道“行政主体”概念。
二,看病交费的,就是买卖关系。这是没把握住民事法律关系的三要素,未弄清交费这个“费”的不同种类,误判也就不奇怪了。[29]
孙淑云在《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立法研究》专著里论及“社会医疗保险中的医患法律关系”,认为,当一个被保险人作为患者去医疗服务机构就诊时,会同时获得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外的医疗服务,患者就此具有双重身份,享受基本医疗服务时,属基本医疗保险的受保障主体;享受基本医疗之外的、由患者自费的医疗服务时,属医患民事合同主体关系。因此,社会医疗保险中的医患关系更多的是既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关系,也同时包括医患民事关系。[30]被其并列于“医患民事关系”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的法律属性,主要是行政法律关系。所以,孙淑云的观点,与笔者庶几相类,只是表述的字面有异而已。刘鑫、连宪杰在《论基本医疗卫生法的立法定位及其主要内容》一文里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做了比较含蓄、但是意思还是可鉴的表达:“如果是以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为基础引发的医疗纠纷,这本身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问题。因此,在法律层面需要特别规定,采取特殊处理。这显然与我国目前医疗模式下处理医疗纠纷的机制是不同的。”[31]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张赞宁提出“医患关系是斜向法律关系”的观点,认为应并列于民事、行政、刑事法律关系。此说有一定的道理。如果医患关系确实特殊到无法归类,那么,再立一类自是理性选择。不过,笔者以为,目前,尚看不出这个必要。
可见,现今的动态是,“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已经成为学界的显学,专文,以及硕士论文选题,多见了。进展,也已从“医患关系是且只能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律民事说”,嬗变为“具有特殊性的民事法律关系”,且,已经能够把“精神病强制治疗”、“法定传染病控制性诊疗”与无因管理等医患关系剥离,承认是行政法律关系了。
在国家规制层面,2005年6月1日起施行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终于有了“国家赔偿”的建构:
第四十六条
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的,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
因接种第一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因接种第二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相关的疫苗生产企业承担。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具体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因接种第一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就是适用的国家赔偿法理,即,认定第一类疫苗接种的医患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一律民事说”实际上已经被抛弃,只是法学界大腕们没有直接针对自己过去的文字和言论认错而已。婉转地告别自己不成熟的过去,也是人之常情,无需苛求的。关键在于,这个理论进展,应该被《基本医疗卫生法》立法工作关注。笔者建议,《基本医疗卫生法》宜明确:“政府举办的以提供基本保障性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为主要职能的各级各类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其法定业务领域形成的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法律关系,其侵权损害赔偿适用国家赔偿法律。”
參考文獻
- 周力、刘住洲.人的尊严之观念史考察--从开端到启蒙.见:张永和主编.中国人权评论.2014年第1辑·总第4辑.法律出版社,2014:21. 返回內文
- 黎江虹著.中国纳税人权利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171~172. 返回內文
- 杨立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精解.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227. 返回內文
- 同[1]:226. 返回內文
- 胡晓翔.浅议《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2):91. 返回內文
- 梁慧星.侵权责任法重要条文解读.见:梁慧星著.中国民事立法评说—民法典、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351. 返回內文
- 曾庆敏主编.法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011. 返回內文
- 曹康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209. 返回內文
- 吴恩玉.中国法律相同位阶及认定.见:胡建淼主编.法律适用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203. 返回內文
- 同[4]. 返回內文
- 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268. 返回內文
- 胡晓翔.拿什么迎接你,侵权责任法?.医界,2010,(8):32. 返回內文
- 吴恩玉.中国法律位阶的几个“灰色地带”.见:胡建淼主编.法律适用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207~208. 返回內文
- 同[10]:270. 返回內文
- 同[6]. 返回內文
- 骆梅英.法律适用规则(一).见:胡建淼主编.法律适用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515、518. 返回內文
- 胡晓翔.在人权保障背景下的思考.见:胡晓翔,姜柏生编著.冷眼观潮----卫生法学争鸣问题探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33、35. 返回內文
- 汪进元等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实施保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202~203. 返回內文
- 刘俊海.论社会权的保护及《经社文公约》在中国的未来实施.见:刘海年主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中国挪威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研究会文集.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38、139. 返回內文
- 鞠成伟.通过社会权利保障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见:江必新主编.行政规制论丛·2011年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1. 返回內文
- 白桂梅、刘骁编.人权法教学参考资料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4、15. 返回內文
- 鞠成伟.通过社会权利保障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见:江必新主编.行政规制论丛·2011年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1. 返回內文
- 鞠成伟.通过社会权利保障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见:江必新主编.行政规制论丛·2011年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2. 返回內文
- 高娣.舆论监督 宪法撑腰.法制日报:2000-4-17:第五版. 返回內文
- 周永坤.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中国法学.1997;(1):22. 返回內文
- 鞠成伟.通过社会权利保障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见:江必新主编.行政规制论丛·2011年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1. 返回內文
- 黄茂钦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治保障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26~27. 返回內文
- 龚向和著.社会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4. 返回內文
- 胡晓翔、姜柏生编著.冷眼观潮-卫生法学争鸣问题探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57. 返回內文
- 孙淑云著.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172~173. 返回內文
- 刘鑫、连宪杰.论基本医疗卫生法的立法定位及其主要内容.中国卫生法制.2014;(3):26. 返回內文
- 本文授權資料來源:两岸医药法治联盟
胡晓翔
-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南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省卫生法学会副会长
關鍵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