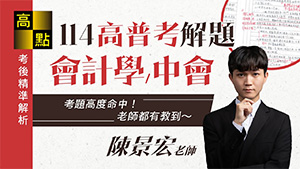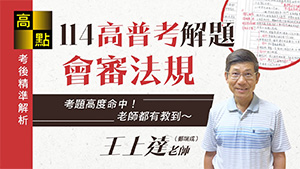壹、前 言
我國於2009年5月20日增訂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10條之1,其立法目的係為賦予保護機構就上市(櫃)公司董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提起代表訴訟或裁判解任訴訟,不受公司法相關程序及持股比例規定之限制,以充分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適時解任不適任董監事。其中,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明文賦予保護機構得依規定為公司對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並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事或監察人。
然而,因實務上對於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進行操縱、內線交易,或有期貨交易詐欺等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行為,是否屬於2020年修正前之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見解不一。故為求明確並強化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2020年修訂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將上述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之行為列舉為保護機構得提起解任訴訟之獨立事由,以杜爭議。
然而,本次修法存在兩點值得探討的問題:首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之保護機構「發現」有違法情事,以及同條第2項規定之保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上述條文所謂「發現」、「知」,其定義為何、其時點如何界定、兩者是否有異同?並不清楚。
再者,投保法第40條之1明定:「本法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然而,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2年度商訴字第24號民事判決等實務見解,均採取擴大解釋溯及適用範圍之見解,將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之適用擴及於第40條之1未規範之修法前尚未提起訴訟之案件。法院此一見解是否妥適,亦值得探究。
綜上,本文將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2年度商訴字第24號民事判決(下稱本件判決)作為引導案例,探討上述問題,並提供評析供各界參考。
貳、案例事實
被告為A公司的實際負責人,並自2018年6月26日就任B公司獨立董事,2021年7月29日經股東會改選續任獨立董事,任期至2024年7月28日,嗣於2023年6月1日因辭職而卸任獨立董事職務。
2019年11月間,C上櫃公司負責人甲有意出售C公司,便於與被告簽立委任服務合約後,委由A公司尋找策略結盟對象。被告嗣於2019年11月19日引介D公司之負責人乙與甲會面,並於12月23日當晚達成C、D兩間公司股份轉換之共識,確定換股比例(該重大消息此時已具體明確為本件判決兩造之不爭執事項)。被告於12月24日指示不知情之A公司員工以被告之妻子擔任負責人之E公司證券帳戶,買進C公司股份;並於同日及隔日由其妻子及兒子分別以被告名下之證券帳戶及另一公司名義,同樣買進C公司股份,共計不法獲利新臺幣1,336,500元。
被告上開行為,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3款之規定,於2023年6月6日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號判決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內線交易罪,處有期徒刑1年10個月確定。
本件判決原告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心),於2023年5月12日起訴,主張被告所為構成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解任事由,其擔任B公司獨立董事之職務應予解任,爰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參、本件爭點
本件判決之核心爭點,即被告從事內線交易之行為發生於2020年投保法修正前,投保中心於2023年5月12日始起訴。本件於新法時期始起訴,應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之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除此之外,雖本件兩造並未爭執,但可以再延伸討論的是:被告內線交易之行為發生於2019年12月間,檢察官起訴時點為2022年12月22日,而刑事一審判決於2023年6月作成並確定。然而,投保中心於2023年5月間,即訴請裁判解任。投保中心得否於刑事判決確定被告犯內線交易罪前,即訴請裁判解任?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所稱「發現」之時間點應如何認定?又同條第2項除斥期間自保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亦存在應如何認定之疑義......(閱讀全文請參考月旦會計實務研究或月旦知識庫)
全文刊登於月旦會計實務研究,第84期:生成式AI強勢來襲引爆新革命 訂閱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