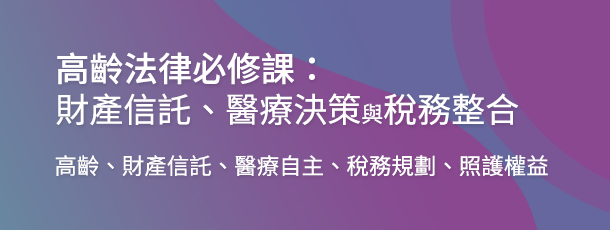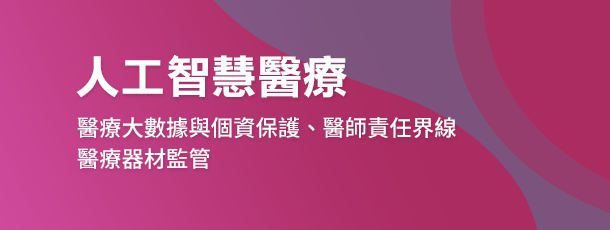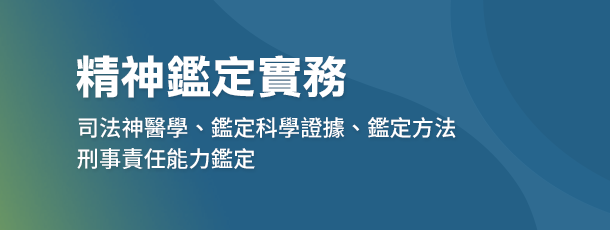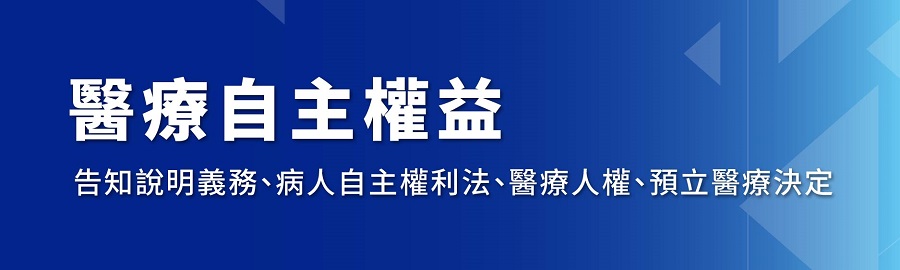原則與例外之間:再生醫療製劑條例草案「附款許可」之方法論與政策分析(醫法新論)
文章發表:2024/05/15
壹、「再生二法」之修法爭議
在臺灣,再生醫療(regenerative medicine)的法制化可謂一波三折。從2018年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在醫療法第62條第2項授權制定「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下稱特管辦法)中,以正面表列式個別開放六類使用自體細胞之細胞治療。但從法規命令層次的特管辦法躍升為正式立法時即爭議不斷,從用於細胞治療之成分究竟是「製劑」還是「藥品」?架構究竟是「三法」抑或是「二法」?到今(2023)年的爭議則轉向再生醫療法(草案)中的免用合格再生醫療製劑即進行再生技術之例外條款(第9條)之條件寬嚴,以及醫院可以執行再生醫療之成果成立生技公司之途徑(第11條),「再生二法」—即「再生醫療法」(草案)及「再生醫療製劑條例」(草案,下稱製劑草案),終究未能於立法院院會第10屆第7會期通過。
與再生醫療法例外途徑相似者,也存在於製劑草案的「附款許可」制度。除了「原則—例外」之間如何拿捏的爭議外,細究其規定產生之疑義或路徑不明之處,不但不亞於再生醫療法之問題,且不利於產業評估發展與投資方向。本文於「貳、」針對其內容與現行「藥事法」及恩慈療法(compassionate use)制度對照,以一般法釋義學觀點剖析目前草案規定之問題。後於「參、」對照歐盟附條件上市許可(Conditional Marketing Authorization, CMA)之經驗與研究建議為主,從經驗上提出整體制度的可能問題,以及更重要的「肆、」,是對醫藥製品「安全性」與「有效性」判斷的知識論層面省思。
貳、附款許可之制度描繪與釋義學的疑義
一、再生醫療製劑之標準查驗登記程序與管制重點
依衛福部製劑草案之修法總說明,「鑑於再生醫療製劑之成分異質性、製程特殊性及治療複雜性,風險管控有別於化學或生物製劑,現行藥事法相關規範無法完全涵蓋或一體適用」故「擬具『再生醫療製劑條例』……草案,作為藥事法之特別法,……」。並於第1條後段明確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依藥事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而依製劑草案第6條第1項,「藥商製造、輸入再生醫療製劑, 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查驗登記,並經核准發給藥品許可證或核予有附款許可後,始得為之。」至於查驗登記應如何進行、標準為何?製劑草案並未進一步直接規定或指示,依其文義即應回歸適用依藥事法第39條第4項制定之「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但該準則第4條只規定「新藥」、「學名藥」、「生物藥品」、「原料藥(藥品有效成分)」及「核醫放射性藥品」五種類型,並於準則第39條到第43條連結使用相關表格之應檢附資料。對照修法總說明指出再生製劑「風險管控有別於化學或生物製劑,現行藥事法相關規範無法完全涵蓋或一體適用」,並沒有在立法層次針對上市前的風險控管之標準或程序予以區辨,連許可證之有效期間都一樣是5年、可展延。
真正與藥事法有重大差異者,是在法律層次上使上市後監管的方式更具體,且明確賦予違反的不利效果。藥事法第45條、第45條之1僅概括授權主管機關得進行上市後監管及不良反應通報,製劑草案第17條要求許可證及附款許可所有人有依公告或核定定期繳交安全監視計畫與報告(且使用製劑的醫療機構亦有提供資料予所有人之義務),不符規定情狀最嚴重者,主管機關得逕廢止其許可證或附款許可。此設計凸顯主管機關對再生製劑的管制架構更著重上市後的安全性監管;相對而言,「上市前」及「上市後有效性」的面向,則與現狀相近。
二、有附款許可
相較於標準的查驗登記程序,製劑草案第6條第2項及第9、10、11條建立前階段審查更寬鬆的有附款許可,其梗概如下:
(一)須為診治危及生命或嚴重失能之疾病之製劑,已依第6條第1項申請查驗登記、並完成第二期臨床試驗 ;
(二)主管機關審查製劑之風險效益,具安全性及初步療效;
(三)決定附款內容(包括執行療效驗證試驗及報告、收費方式、不良反應救濟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四)經「再生醫療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核予有附款許可;
(五)有附款許可期間不得逾5年、不得展延。但可於履行附款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查驗登記並經核准後,發給藥品許可證。
上述制度特徵中,不乏主管機關未明確解釋之草案版本間之改動,以及與既有藥事法規定關係不明之處。
(一)主管機關不得展延,但可否「重複∕再次」核予有附款之許可?
於「再生三法」時期所提出「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草案版本中第8條第2項,明文禁止中央主管機關「重複」核予有附款許可。立法理由認為,附款許可為權宜措施,原許可逾期後即應回歸正途,循標準查驗登記程序完成三期試驗取得藥品許可證。但製劑草案中刪除本項規定,主管機關並未說明是認為「不得展延」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必然包括「不得重複或再次」核予附款許可?亦或是改變見解,已開放再次核予有附款許可之空間?但如此一來,即有論者主張將實質架空「5年、不可展延」之制度本旨。
具體而言,可能的案例是某款製劑通過二期後先申請附款許可,期限結束後依法不得展延,故回歸標準查驗登記程序,卻遲遲無法順利通過臨床第三期的僵局。此時藥商若再次提出附款許可之申請,即非原許可之展延。由於展延與重複字義鮮有落差,主管機關此時若僅憑「舉輕以明重」之法理一概拒絕藥商之再次申請,不論該法理是透過長官指示或另制定裁量基準實現,均可能構成「裁量怠惰」而在行政救濟中遭行政法院認定原處分、乃至其所依據之基準本身均違法。但若主管機關是有意重複核予有附款之許可,則其見解改變理由為何?考量歐盟運作經驗,更擴大附款許可之空間恐怕造成例外侵蝕原則之現象(詳見後述)。
(二)主管機關如何評估風險效益?論消失的「無替代」標準
製劑草案第9條規定製劑「於完成第二期臨床試驗,並經審查風險效益,具安全性及初步療效者,得附加附款。」主管機關於立法理由中說明:「得考量病人生命之危急性與失能之嚴重度、診治效益及風險,確保安全性及初步療效後,核予附加附款且有效期間不超過五年之許可……提升病人用藥之可近性」。相較於更早期之版本,此處刪除了「(國內)尚無適當藥物或替代療法」之要件,但主管機關亦未於立法理由中說明原因或考量。此處衍伸問題是,主管機關將如何評估風險效益?可考量與應考量之要件具體為何?可否仍將「有無適當藥物或替代療法」實質納入風險效益審查之標準?
首先,臨床試驗之第一期(phase I)與第二期(phase II)之設計目的,本來就是為了在有限的受試者人數內初步探索安全性與療效,而在第三期(phase III)「確認於第二階段中所得藥品用於目標適應症及受試驗者是安全及有效的初步證據。這些試驗的目的在提供核准藥品上市之適當依據。」 主管機關在不進行額外試驗的狀況下,自無法取得其他數據來衡量該製劑之安全性與療效,故此時的審查重點,是在抽象層次上評估該製劑之潛在療效與風險,對比其適應症對病人帶來生命之危急性與失能之嚴重度。
然而,這樣的衡量在刪除「尚無適當藥物或替代療法」後要件後應如何進行?這恐怕意味著主管機關對於「製劑療效之潛力」對比「適應症危害加上製劑本身的可能風險」須存在著一個通過與否的閾值(threshold)。但若將風險高低視為相對的概念採取反面思考,當國內已有其他適當藥物或替代療法,則對病人而言已無「用藥可近性」的問題,此時仍放行權宜措施而核予附款許可,除了「促進產業發展」以外,其正當性為何?
這個問題在製劑草案與藥事法之間關係不明的狀態下更形嚴重。因為藥事法第48條之2第1項「專案核准」制度,即在第1款規定「為預防、診治危及生命或嚴重失能之疾病,且國內尚無適當藥物或合適替代療法。」(黑體為作者加註)之許可條件。立法理由固然明示製劑草案是藥事法的特別法,但「附款許可」(製劑草案)與專案核准(藥事法)之間是否應視為對相同事實類型的規定而優先適用特別法?抑或視其為「本條例未規定者」而仍保留再生製劑採專案核准模式使用?又,在立法理由未載明刪除考量下,主管機關可否將其他適當藥物或替代療法納入風險效益的評估因素中?若再將第1項第2款「因應緊急公共衛生情事之需要。」之專案核准事由併入,則更能凸顯此處所採法律解釋方法之兩難:以新冠肺炎為例,其大多屬於輕症但能大規模感染傳播,恐累積出拖垮醫療量能重症病患之特性,固不構成附款許可「危及生命或嚴重失能」之要件,卻有從公衛政策角度介入之必要。故若有完成二期試驗之再生製劑能極有效預防或治療新冠肺炎,則若不承認藥事法下專案核准制度仍可能適用於再生製劑,即無法提前使用該製劑對抗疫情......
全文刊登於月旦醫事法報告,第88期:醫療器材管理法制與商品責任 訂閱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