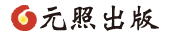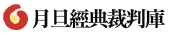從駐馬店男子被“精神病”醫院被判精神損害賠償談
文章發表:2017/07/04
王丽莎
成年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医疗实体要件
编者按:
2017年7月3日,余某被妻子等人强行送入驻马店市精神病院住院治疗19天的案件,法院一审认为驻马店市精神病院侵犯余某人身自由权,判决院方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2015年10月8日,因与妻子婚后感情不和,38岁的河南男子余五在签署离婚协议的当天,被妻子及亲属强行送入驻马店市精神病院。随后,院方以“性偏好障碍”的名义将余五收治,并对其进行治疗,前后共计19天,最终,余五在警方协调下出院。
2016年5月17日,余五将驻马店市精神病院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昨日,驻马店市驿城区法院下达判决书,一审认定驻马店市精神病院的强制治疗,侵犯了余五的人身自由权,判决院方公开道歉,并处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元。
如何界定?
我国《精神卫生法》第30条第2款规定:“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与此前《精神卫生法》(草案)相比,该法删除了“不住院不利于其治疗”。其他国家和地区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医疗的实体要件通常为:具有精神疾病、有自他伤的危险性、有医疗的必要性以及有治疗的可能性。患有精神疾病是讨论精神障碍患者相关问题的应有之义,不再赘述。非自愿住院医疗不仅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住院期间患者的隐私权、通信、会面等权限也将或多或少受到限制。出院后更是会被标签化为“疯子”或“傻子”,受到社会其他成员的排挤、歧视。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必须满足实体正当的要件。我国实施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住院制度时,是否也需要医疗必要性和医疗可能性要件,值得探讨。本文试图通过对各国非自愿医疗实体要件的比较研究,分析该制度的法理基础,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医疗的实体要件。
一、自他伤的危险性
自他伤的危险性是警察权思想(Police power)的体现。警察权思想是指为了防止精神障碍患者对社会秩序造成危害,必须在患者具有明显危险性时,强制其住院治疗。在德国,精神障碍患者的问题都是适用《警察法》在处理的。这种做法根植于普鲁士一般邦法,为了维护大众的安宁、安全与秩序,避免大众收到即将发生的损害,授权警察在特殊情况下可将患者收容在必要机构。以此思想出发,会较为注重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此派认为只有在精神障碍患者行为对于自身或他人具有明确可见的危险性时,才可以正当化对自由的剥夺。针对危险性的判断,需要很多客观证据加以判断,只有在具备足够证据可以证明精神障碍患者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极大可能性会对他人或自己造成伤害时,才能正当化强制化强制住院。美国法院针对强制住院问题,在许多判决上都采取这个标准。
我国《精神卫生法》中“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的规定,虽然涵盖了已经发生自他伤的行为和具有自他伤的危险两个层面,作者认为,已经伤害自身的行为可以纳入自他伤的危险性要件中,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则可能触犯《治安处罚法》或《刑法》,不考虑患者意愿将其置于精神病院或公安系统下的安康医院,其实体标准和程序应适用《刑事诉讼法》“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
然而,精神疾病的判断容易流于主观已经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危险性”的预测更是十分困难,因此,美国精神科医师也察觉到这种过度预测的问题,并戏称此种预测是一种可伸缩自如的“魔术文字(Magic Word)”。为了解决此技术上的问题,美国司法判决自1970年以来,不断地将强制住院程序规格提升至刑事诉讼程序般的水准,也是着眼于对于将来预测的地精确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强制住院程序的证明程序,只是必须达到“明白、确信的程度(clear and convincing)”,大约75%的精确程度。另外,许多判决均要求必须提出客观证据用以佐证对象者的将来危险性。日本措置入院的程序中,鉴定医师必须填写的鉴定文件中,也备有“问题行动”一栏,目的也在于提供判断着有一客观事实预测其未来危险程度。然而,尽管临床上有许多预测未来危险性的科学方法,但其终究只是一种几率的评估,存在误差也是必然的。甚至日本有学者认为,以将来危险作为强制住院的理由是违反宪法的。但是,强制收容精神障碍患者贯穿整部人类近代历史,我们或许应该另觅出路,以父权思想出发的医疗必要性出现了。
二、医疗必要性
医疗必要性主要体现了父权思想。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在危及自身生命时,有时不具有能力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此时由法律现行强制其入院,以达到保护患者利益的目的,这就是父权主义思想(Paternalism)。这种概念深植于西方文化之总,期思想起源可以追溯至罗马法时代。父权思想具有为了保护本人自身利益,进而干涉其自由的基本特征,所以,精神障碍患者利益的保护与其自由意志间的拉锯战无疑是这个领域中最难解决的问题。现在对于人类基本人权的看法认为所有人类都是自律存在的个体,必须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即除了最常见的人身自由不可任意侵犯外,还包括人类最为重要的心灵层面也不容随意侵犯。选择的生活模式以及价值观,即使其所选择的道路在旁人看来有所不当,但是在这样尝试错误的经验之后,各式各样独特的人格特质方可形成。
自父权思想出发的主要是精神医学者,他们的立场在于治疗、照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模式。他们认为,患有精神障碍的患者无法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他们需要接受治疗,否则最终将会伤害自己与其他人。因此,此模式为非自愿住院设置的检验标准倾向于要求必须具有精神疾病、对于生活功能的阻碍以及有照护治疗的需要。美国在19世纪首次将医疗必要性要件运用于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住院的制度。当时,近代精神医学正蓬勃发展,人们普遍相信医疗对于精神疾病具有高度治愈率。以治疗为目的的非自愿住院形式开始出现,精神病医院于此时快速增加,美国各州也开始扩大强制住院的对象,除了危险性显露于外的精神障碍患者外,也将治疗有望的精神障碍者大量纳入精神医疗保护网之内。美国最高法院1845年作出的Oakes判决对此要件给予正面、肯定的回应,认为国家之所以可以拘束精神障碍患者,是因为放任精神障碍患者游荡社会会存有危险的人道法(the great law of humanity)思想。而各州也开始在危险性要件之外,将“医疗必要性”纳入州法。以此要件为中心的强制住院制度便在精神医疗领域称霸往后一百年的岁月。然而,在这段时间,许多人发现有些客观上非精神障碍患者,却因此被强制住进医院,为了防止此种现象,开始出现程序严格化的主张。1960年代后半,精神障碍患者人权收到重视,危险性要件逐渐在美国法制度中夺回主导权。但是不久之后,人们又开始深受被释回社会的精神障碍患者的困扰,“医疗必要性”为要件的声音又再次复活,可以说,医疗必要性和危险性要件的战争从未停歇。
实际上,这种治疗必要性的判断,有多少客观证据可以加以佐证,是很难回答的。如果对医疗必要性不加以限缩的话,很可能出现即使是轻微的症状也被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情形,这是否是精神障碍患者的最佳利益,颇值得商榷。我国《精神卫生法》对非自愿医疗规定了“严重精神障碍”的条件,并在附则中进行了解释:“严重精神障碍,是指疾病症状严重,导致患者社会适应等功能严重损害、对自身健康状况或者客观现实不能完整认识,或者不能处理自身事务的精神障碍。”因此,此规定既体现出疾病需要医疗照护的必要性,又以“症状严重”的客观标准加以限定,属于限缩后的治疗必要性要件,有助于破解医疗必要性与危险性要件的矛盾。
三、治疗可能性
不管是基于父权医疗照护的思想,还是警察权防卫社会的考虑,将患者非自愿收容于精神病医院,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治愈患者的疾病,防止其对社会再次造成危险。那么,当精神障碍患者的疾病不具有治疗可能时,是否可以强制其入院呢?
英国是实施开放性治疗精神障碍患者的先驱,根据其《精神保健法1983》的规定,如果医院认为患者“治疗不可能(untreatable)”,可以拒绝其入院。对于精神障碍犯罪者,法院在是否宣告其进入医院接受治疗时,也会考量治疗是否可能等因素。该要件的设定原本是针对人格异常者,对于可以在医院内有效改善的就让其接受治疗,治疗成效不明显的则由其他渠道加以管制。但是,这一要件也引发了很多批评。1998年一名年幼即不断犯罪,且有药物中毒现象的38岁男子,杀害了一名陌生女子一个6岁的小孩被判终身监禁。在此案发生前,该男子被判定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严重精神病质人格到精神科就诊,但由于精神病质人格不具有治疗可能性而被拒绝入院治疗。因此,英国开始出现以治疗必要性取代治疗可能性的看法,且认为危险性高的精神障碍患者必须适时地被拘束。而为了适应这种拘禁,应当有精神病医院和监狱之外的其他的收容机构。
如果以治疗可能性作为强制住院治疗的要件,就可能面临对于社会秩序有危险的患者,因为没有治疗的方法而释回社会,造成与社会秩序维护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欧洲人权法院对于此要件中的“治疗”概念的解释才如此扩张且充满争议。1967年,在Reid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Scotland 案中,Reid(被诊断为人格异常)杀人罪名成立,被关入精神病医院。1994年7月,Reid向法院申请出院,法院以其再犯危险性仍高位由,拒绝其申请。Reid 根据1984年《精神保健法》第17条第1项中“患有精神障碍,有异常攻击行为或无责任的行动时,以治疗减轻、防止其症状恶化”为强制住院的要求,主张既然入院时以“治疗可能性”为判断要件,出院时此要件的有无也是关键所在,进而主张自己已经没有治疗的可能性要求出院。审理此案的英国苏格兰贵族院认为,所谓的“治疗”,病不仅限于有效改善患者症状,只要可以减轻、防止疾病恶化,就可以成为治疗。并认为,Reid在医院里,由于环境、作息安排等,控制自身情绪的能力增加,这就可以认为其具有“治疗可能性”,而否决了其出院的要求。
1999年,英国针对治疗可能性进行修法,Reid此时再次申请出院,仍被拒绝。因此,Reid 连同其他三名患者,向欧洲人权法院主张原贵族院的判决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1项e款。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强制收容不仅限于为了治愈患者症状或者减轻其症状而需要临床治疗的情形,还包括为了防止自他伤的危险,而必须加以管理、监视的场合。因为人格异常者再犯危险很高,因此贵族院拒绝Reid 出院申请并不违反公约。而且,即使不具有治疗可能,对于Reid来说,被拘禁于医院中,由于环境良好对其也有益。
其实,欧洲人权法院对于“治疗”概念的扩张性解释,已经暗度陈仓地将保安目的带进“治疗可能性”的概念之中。将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入院治疗,除了解除迫在眉睫的危险外,另一重要目的则是借由医疗手段,缓解精神疾病症状,进一步消除其对他人、自身的危险。尽管如此,由于我国目前医患关系十分紧张,患者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极为不信任。将“治疗”做扩大解释,可能激化患方乃至全社会对医疗机构的误解。因此,作者认为,我国“治疗可能性”要件应当采取限缩的解释,应当理解为医学上可以“治疗”。对于上文提到该要件与维护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某种程度上有过度忧虑的嫌疑。担心没有治疗可能性的精神障碍患者会造成对他人的严重危害,是因为社会大众普遍认为这些患者具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危险性。但是,我国台湾地区的统计资料显示,由精神障碍患者引发的犯罪事件,远不及所谓正常人所引发的犯罪。因此,对“治疗”作限缩性解释,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
人类社会拘禁精神障碍患者的初始目的只是消极隔离,不带有治疗、照护的目的。历经多次改革,精神障碍患者人权保障有了明显的进步,虽然多数强制住院治疗制度仍以患者的危险性为要件,但是,作者认为危险性要件的主要目的在于限缩国家公权力介入的空间,现今世界精神医疗潮流仍以淡化保安色彩为主要诉求。既然如此,将没有治疗希望者,单纯因为未来危险而长期拘禁的作法,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因此,尽管我国《精神卫生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治疗可行性”要件,窃以为该要件应当是精神障碍者强制“医疗”的应有之义。
四、结语
其实,不论基于何种思想,采取何种模式,学者们都是以各学科的内在价值诠释当代社会控制的技术。父权思想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欠缺自我思考能力者的最佳利益,警察权思想则主要在于维护社会整体安全和秩序。二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现今各国法制多将两种理念加乘以构筑相辅相成的法律制度。我国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医疗的实体要件规范中,同样体现了这两种思想,不过,现有法律规定中,不仅要对自他伤危险性与医疗必要性加以规范,还应当扩大解释为含有治疗可行性的要件,对于医疗行为不能够控制或改善病情的精神障碍患者,应以非拘禁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
作者长期关注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医疗制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曾担任河南省精神病院伦理委员会委员,先后于2010年、2014年主持四川省医事卫生法治研究中心研究课题“精神医疗侵权中的法律问题研究”、“民法视角下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医疗制度的实证研究”,2014年主持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科学研究课题“精神障碍患者自我决定权的民法保护”,2015年主持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成年精神障碍患者行为能力研究”。
现将曾经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章刊发至此,分享对于此类患者权利的保护以及对“被精神病”的防范。
- 本文授權資料來源:医药健康报告
王丽莎
-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北京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卫生法学理事、中国医师协会医学人文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本科曾学习临床医学,从事医学法学交叉学科理论、实务工作11年。
- 电话/微信:15120007769
- 邮箱:liza52534@126.com
- AI醫療的倫理規範與責任釐清 12/8
- 醫療器材管理法的制度革新與風險治理 12/1
- 醫病關係的安全挑戰 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