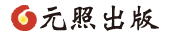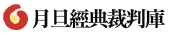淺析醫務人員的避險保護
文章發表:2021/04/01
樊荣、万晓君
“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马丁·路德金
一、相关案例
2018年3月23日,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李医生深夜出诊在急救现场询问患者病情,之后让其签字时,两次被自称是病人“家属”的酒后男子殴打。在男子对其殴打过程中,他不仅没有还手,仍坚持查看患者,并劝其进院就诊。醉酒殴打医生的男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0天。事后李医生说,“莫名被打,确实有些生气,但作为一名医生,我是治病救人的,院领导经常强调一定要做到‘患者至上’。所以在被打的过程中,我没还手,只能用手护着脸。”
2019年2月9日,四川乐山一醉酒男子到五通桥区人民医院眼科就诊。因男子不停打瞌睡且说不清病情,刑医生建议其等家属前来再治疗。但该男子对刑医生一顿暴打,而刑医生忍住疼痛,不计前嫌为男子治疗。事后,男子被警方行政拘留7日,罚款400元。医院给刑医生颁发了1000元“委屈奖”。
2019年10月15日,一酒后摔伤患者由朋友陪同至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人民医院急诊室就诊。值班医生刚开口了解伤情形成原因,醉酒后的患者朋友情绪激动失控,无故辱骂、殴打急诊科值班医护人员。医生前来带领患者前往手术室的过程中,男子又是对他拳打脚踢。但被打后的宋医生丝毫也不生气,不计前嫌,忍气吞声,有条不紊开展治疗,为患者清创缝合。事后,打人男子因寻衅滋事被齐河警方行政拘留。齐河县卫生健康局党组决定,把宋医生作为对标对表学习的先进典型,号召全县卫生健康系统学习他高尚的医德医风。
被暴力殴打下的“患者至上”、“委屈奖”和“先进典型”,无疑是全国医务人员面孔上的一个“苦涩的微笑”。就连2500多年前的孔子都教导弟子,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应“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而如今,面对暴力伤医,手无寸铁的医务人员却依然只要通过忍气吞声,来维护“救死扶伤”的职责与医德吗?“白衣天使”、“活菩萨”等高尚称呼与“圣人”构象,实际上已对医务人员造成了沉重的捧杀。
对于暴力伤医,2014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等5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明确了六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将暴力伤医入刑。但对于受伤害的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一方,除了及时报警处理,却没有任何政策规范和实践指南。广大医务人员面对伤害,仍然只能以崇高的医德标准,作为唯一的行动指南,显得既可贵又可悲。可贵的是面对如此苦难,医者仍凭着当初的一腔热血和崇高信念在坚持坚守;可悲的是面对如此困境,医者的坚忍并未换取环境的好转,伤医事件仍时有发生。2020年1月20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陶勇医生在出门诊时被患者持刀砍伤。陶勇说,“不把自己埋在仇恨之中,不代表我可以宽容他、谅解他。否则这也是对其他医务工作者的道德绑架。”这可能才是医务人员最真实的感受。
因此,面对暴力伤医,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应如何避险保护呢?
二、从“拒绝诊疗权”到“紧急避险权”、“回避诊疗权”的立法探索
(一)“拒绝诊疗权”
关于该问题的解决,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最初的探索是希望明确医方的“拒绝诊疗权”(简称“拒诊权”),即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有权拒绝为特定的患者提供诊疗服务。但该探索一直存在巨大的争议。
一方面,部分医务人员认为诊疗权是其自身的权利,那么既然有权利提供诊疗,则同样也有权不提供诊疗,即有权拒绝诊疗,尤其是针对暴力伤医行为。《美国医学会医疗伦理守则》规定:“对医生、护士、其他病人进行暴力威胁或攻击”、“对医护人员展示明显的、足以妨害执业的敌意”时, 医务人员可以终止医患关系,同时“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事先通知患者或负责的亲属, 使之有机会确保能继续受治疗”。加拿大医学会的《医师伦理准则》规定,医师的个人价值观能明显影响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时,可以拒诊。这里的个人价值观应主要包括宗教信仰、种族偏见等明显价值歧见。而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医师伦理准则》中规定,当医师与患者的信任关系已经破裂时,医师可以终止诊疗关系。破裂的理由包括患者要求医师从事欺诈或非法活动,或者对医师进行攻击行为 。近年来,已有多家医疗机构发生过对暴力伤医采取拒诊的情况。2014年8月27日,复旦大学儿科医院骨科出现医闹,骨科主任在微信中发表郑重声明,率科室拒诊。4天之后,湖南省岳阳市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出现医闹,急诊科主任发出倡议,岳阳市“全市急诊同仁”将3名伤医凶手拉入黑名单,在该事件得到合理、公正、圆满解决前,拒绝为之提供任何医疗行为。
另一方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与《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均对“不得拒绝急救处置”的义务进行了明确,说明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有强制缔约义务,无权拒绝诊疗。而日本《医师法》则更是将医疗上的强制缔约义务进一步扩展至所有诊察治疗请求存在的场合,即若无正当事由,即使非紧急情况,亦不能拒绝诊疗 。有学者 将医师“不得拒绝诊疗”的义务概括为:医师对于患者,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医学伦理的角度,都有必须诊疗的义务,在医师的工作时间、工作范围内,有条件救治的,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或延迟救治,也被称为强制缔约义务。医疗机构的强制缔约义务,是指医疗机构负有应患者请求,与之订立医疗服务合同的义务。医疗机构强制缔约义务是指患者一方如果向医疗机构提出合理医疗请求,作为受要约人的医疗机构应对此种要约作出承诺的义务。医疗机构强制缔约义务是契约自由领域中对契约一方当事人意志自由的限制 。我国也有多名学者提出医疗机构应当承担普遍的强制缔约义务,不问患者是谁,也不问患者病情的危急程度,医疗机构若无正当事由,对患者的缔约请求均不能拒绝 。医疗机构作为垄断性和公益性的代表,鉴于其行业特殊性,不得拒绝诊疗的义务则是必然的。
二者相互矛盾,同时也存在立法不明。因为“不得拒绝急救处置”并非针对所有诊疗场合,故也被称作紧急情况下的强制缔约义务,是有限定范围的。因此,另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局限性的强制缔约义务正是说明是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不允许对所有患者均负担强制缔约义务 ,即可以有限的拒绝诊疗。其核心在于医疗机构拒绝诊疗时,是否具有正当事由。理论上将正当事由的情形主要分为医方原因、患方原因和不可抗力原因。医方原因主要包括患者所患疾病超出其执业范围或超出其设备技术条件、医师不在工作场所或因病无法提供、医师人身安全或人格尊严受到危害而无法保障救治能力和水平(如涉医违法犯罪行为)等情形;患方原因主要包括就诊时刻已逾越诊疗时间、患者未支付诊疗费用、患者的要约请求不合法、患者的请求违背公序良俗、患者的请求超出了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患者的请求超出了诊疗常规、患者提出要约的方式不合法等情形;不可抗力原因主要包括火灾、地震、气象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医疗无法正常进行的情形,亦属于正当事由。另外需要考虑的细节是,若患者家属或陪同人员施暴,医务人员可否对患者本人拒诊。这应取决于医务人员与患者的信任状况。如果患者对暴力威胁行为进行劝阻或表示歉意,始终保持理解信任医务人员,则医患关系尚未破裂,不应拒诊。如果患者支持赞同或怂恿鼓励施暴行为,则医患关系破裂,支持拒诊。
正因存在以上争议,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在工作时间、工作范围、工作场所、有条件救治的医疗机构具有“非正当事由不得拒绝诊疗”的义务。义务与医疗机构有密切的关系,而并非属于医师身份的附随义务 。当有正当事由时,足以确认医患关系破裂,医师可以选择拒诊。当某位医师拒绝为患者提供诊疗时,不能扩展至其他医生也拒绝诊疗,这是对医务人员的过度保护,同样并不等同于医疗机构拒绝诊疗,医疗机构若无正当事由则应更换其他医师为患者继续提供诊疗。但关于“拒诊权”始终争论不断,未有最终定论。以上仅为法理推论,国家始终没有相关政策法规文件对此进行明确。
(二)“紧急避险权”
近年来,学界逐步开始尝试通过“紧急避险权”来代替“拒诊权”仅对暴力威胁单因素下医务人员的回避行为进行解释,目的是“自保”,而不是“反抗”。此处的“紧急避险”并非刑法上的“紧急避险行为”,不涉及对第三人权益的损害,仅是对紧急危险情况的回避,属于非典型的自助行为。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二条,“从业人员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作业或者在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在前款紧急情况下停止作业或者采取紧急撤离措施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医疗机构生产服务,也属于生产经营单位。医务人员也属于从业人员。因此,学者认为该条款可以作为医务人员面对暴力威胁下回避行为的合法性依据。医务人员的离开不是拒绝诊疗,而是对紧急危险情况的回避。
但也有学者认为,根据刑法的规定,为了避免本人危险而采取紧急避险的行为,不能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也就是说对正在发生的危险负有特定职责的人,不能为了使自己避免这种危险而采取紧急避险的行为。这里所说的“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是指担任的职务或者从事的业务要求其对一定的危险负有排除的职责,同一定危险作斗争是其职业义务,包括消防队员、医生、护士、船长、海员、民航驾驶员、防汛员、警卫员、警察等的职业义务。因此,认为医务人员没有“紧急避险权”。
笔者认为,根据《执业医师法》,所谓“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针对医务人员是指面对急危患者的紧急救治以及自然灾害、传染病流行、突发重大伤亡事故及其他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紧急情况下的服从调遣。因此,所谓的“紧急危险情况”是指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情况,而并非严重威胁医务人员的情况。医务人员的“紧急避险权”,是紧急回避自身危险,而非回避他人的风险,切不可混为一谈。在自然灾害、传染病流行、突发重大伤亡事故及其他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紧急情况下,医务人员理应服从调遣,但并不应以牺牲自身生命为前提。在抗震救灾中,即使是最专业的救援部队,也不允许在余震来临时继续在摇摇欲坠的废墟中开展救援。《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了医务人员具有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获得执业相当设备条件(含个人防护物资条件)的权利。《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四条也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在国际通行的基本生命支持技术中,现场急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确认现场环境安全”。因此,当医务人员在行使职务行为过程中,其人身安全受到暴力威胁时,医务人员采取紧急避险行为是合理合法的。
(三)“回避诊疗权”
此外,还有学者从患者安全的角度,对医师的避险行为解释为“回避诊疗权”。因暴力威胁具有明显的敌意,已导致医务人员无法开展正常诊疗。参照司法实践中的回避制度,面对暴力威胁,医务人员在无正常的诊疗环境、无法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作为对患者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应该参加诊疗,无法开展正常的医疗行为,否则可能将影响患者得到公平、及时、合理、规范的诊疗。因此,医疗机构从保障患者安全的客观需要出发,也应另行安排诊疗。
(四)北京市的地方立法探索
2020年3月26日,《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交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草案》的第十二条是关于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的避险保护,“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受到暴力威胁时,可以采取避险保护措施,回避对就诊人员的诊疗,医院应当另行安排诊疗”。这是我国首次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对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的避险保护进行的明确规定。该条款从医务人员“紧急避险权”及“回避诊疗权”的角度进行规制说明,更加凸显了其正当性与合理性,同时也避免了在“拒诊权”问题上的争议,获得了广泛支持,也为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面对暴力威胁的应对措施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三、避险保护条款理解与浅析
(一)条款规定“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受到暴力威胁”。“医务人员”包括从事诊疗相关工作的医生、护士及医技人员。此处的“暴力威胁”应理解为《草案》第十四条所规定的七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即“①威胁、恐吓、侮辱、谩骂、推搡和恶意尾随医务人员,以大声喧哗、吵闹等方式扰乱医院正常秩序;②殴打、伤害医务人员;③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④携带枪支、弹药、匕首等管制器具和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以及公安机关规定的其他禁带物品进入医院;⑤非法占用、故意损毁医院财物;⑥借医疗纠纷故意扩大事态、敲诈勒索,在医院及周边违规停尸、设灵堂、摆放花圈、阻塞通道、聚众滋事等行为;⑦其他扰乱医院正常秩序的行为。”暴力威胁的实施者既包括患者本人,也包括患者家属及陪同人员。此处的“受到”,是指以上涉医违法犯罪行为已实际发生,而不包括存在暴利威胁的隐患或风险。例如,医务人员不能因某患者既往发生谩骂行为,存在再次谩骂风险而拒绝为其诊疗。
(二)条款规定“可以采取避险保护措施”。“避险保护措施”应包括回避诊疗、正当防卫、报告科室上级、上报医院保卫部门、报警处理等。“可以采取”则代表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可以自行选择采取或不采取以及采取某一项或某几项避险保护措施。不同的医务人员面对不同程度的暴力威胁,其心理承受能力、矛盾化解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均有不同,因此不同暴力威胁与避险保护措施之间不存在必然性,也并非完全一一对应关系。
(三)条款规定“回避对就诊人员的诊疗”。此处的“回避”指的不仅仅是暂停诊疗,而是通常使医务人员与患方之间进行隔离,避免继续正面接触而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不仅包括医务人员自行离开,还包括必要时由其他医务人员、保卫人员、警察等第三人协助进行的双方隔离。
(四)条款最后规定的“医院应当另行安排诊疗”。此处的“另行安排”,包括另行安排医务人员、另行安排时间或二者兼有。例如,医患之间发生争吵时,可先劝说双方冷静,停止争吵,再另行安排该医师其他出诊时间继续诊疗。再如,醉酒患者扰乱医疗秩序,可暂停诊疗让其先行隔离醒酒,待安全威胁消失后,应及时恢复诊疗。若患者病情危及生命,则应另行安排其他医务人员及时诊疗。
综上,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避险保护的法律规范,其最终目的是寻求患方健康救治与医方暴力自助之间的平衡。当患者、患者家属或陪同人员对医务人员实施暴力威胁,侵犯其人身安全,视其严重程度,医务人员可以采取回避诊疗、正当防卫、报告科室上级、上报医院保卫部门、报警处理等紧急避险措施。医疗机构应另行安排医务人员或另行安排时间为患者继续诊疗。对于急危患者,不得延误救治。也希望以此次北京地方立法为契机,借鉴国外立法经验,逐步完善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有限的拒诊权,进一步实现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保障及良好诊疗环境秩序维护。
当然,更为之有效的避险并非是在暴力威胁下的回避,而是在矛盾纠纷发生之前的及早识别与预防。正如本·富兰克林所言,“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
原文出處: 2020年7月24日中國衛生人才網
https://www.21wecan.com/rczz/al/ptxx/202007/t20200724_9235.html
- 中醫 vs 西醫法律責任探討 2/2
- 《人工智慧基本法》三讀通過,醫療責任如何界定? 1/14
- 中草藥安全別輕忽:天然之下的法律風險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