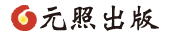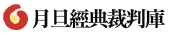當“不當生命”之訴涉及倫理和公共政策,“不當生命”請求權如何突破?
文章發表:2017/09/09
王丽莎
摘要
“不当生命”之诉因涉及伦理和公共政策,而遭遇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否定。然而,“不当生命”请求权的肯认是保护先天残疾儿童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在突破了公共政策、是否构成侵权以及损害赔偿范围难以确定的困境之后,“不当生命”请求权可以形成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请求权主体是先天残疾的儿童;请求权的要件应当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请求权范围通过原因力的比较,可确定为儿童的教育、训练的特殊损害的50%。
导言
由于医生的过失未能发现胎儿存在严重畸形或其他严重残疾,因而未能给予孕妇合理的医学建议,最终导致先天残疾儿童出生的情形,依据不同的权利主体,在美国的审判实践中将其为“wrongful life”和“wrongful birth”之诉。冯·巴尔教授认为,“不当生命”是一个不幸的美国称呼。因为,“wrongful life”这个词,其实很容易让人误解,显然,不当的是过失,而不是原告的生命。但是,这个词太过普遍以致于不得不使用。王泽鉴教授也主张,“所谓Wrongful life问题。原则上应采否定说”。“wrongful life”,可以译成中文“不当出生”,它在普通法司法领域是受到反对的,指的是由于医疗过失而出生的残疾的原告因为他(她)所承受的疼痛和痛苦以及生活的成本,而起诉有过失的医生。尽管,英美国家的“wrongful life”还存在另一种情形,那就是健康孩子提起的往往是与“私生”的耻辱有关,如美国Zepda v. Zepda案。这不是作者要讨论的内容,这里要探讨的只是原告主张,如果没有医学照顾提供者的过失,妊娠将会终止,婴儿将不会生活在这样低标准的情况——一种被贬低的地位下,因此他应当获得赔偿”。
对此,我国有学者认为,这是“非常典型的医师违反产前诊断义务”,进而探讨“医师违反产前诊断义务的赔偿责任”。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赔偿责任是从义务人的角度进行规范的,从保护权利的角度展开讨论,就必然涉及到请求权的问题。民法中的权利和义务所指称的是同一个法律关系的内容,二者的区别只在于主体的不同。正因如此,在权利的救济问题上既可从权利人的角度以请求权的形式探讨“权利的救济”,亦可从义务人的角度以责任形式研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然而,“不管立法上采取的是请求权模式抑或责任模式,学理的任务并不会因此减轻,因为即便是采取了责任模式,责任模式的背后仍然存在着请求权及请求权体系。”所以,即便已经对义务人的民事责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由于民法是“权利法”的本质,对于权利人请求权的问题依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肯认“不当生命”合法性的现实意义
根据我国《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育龄妇女和孕产妇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对孕育健康后代以及严重遗传性疾病和碘缺乏病等地方病的发病原因、治疗和预防方法提供医学意见;对患严重疾病或者接触致畸物质,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或者可能严重影响孕妇健康和胎儿正常发育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予以医学指导;经产前检查,医师发现或者怀疑胎儿异常的,应当对孕妇进行产前诊断;医师发现或者怀疑育龄夫妻患有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应当提出医学意见;限于现有医疗技术水平难以确诊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情况。育龄夫妻可以选择避孕、节育、不孕等相应的医学措施等。然而,2002年7月1日我国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实施的《中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和残疾行动计划(2002-2010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肉眼可见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
也就是说,经过了产前检查和产前诊断后,依然有这么多先天残疾的儿童出生。除了医疗水平和基因检测技术的限制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医生由于过失没有发现胎儿存在先天的缺陷,从而未能给与孕妇夫妇终止妊娠的医学建议,使孕妇以为胎儿发育健康正常而产下实际上具有先天残疾的孩子。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残疾儿童的生活和学习所需的各种特殊费用,国家无法负担。这种背景下,应当肯认残疾儿童的“不当生命”损害赔偿请求权,才能为其以后的生活提供物质上的保障。
有学者认为,如果孩子可以单独提起侵权之诉,在诉请的损害赔偿范围上会与父母提起的赔偿请求发生重叠,而给予双重赔偿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孩子和父母具有独立的人格,医师的过失行为对于他们的损害也是不同的。之所以可能“在诉请的损害赔偿范围上会与父母提起的赔偿请求发生重叠,而给予双重赔偿”,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于“不当生命”和“不当出生”的请求权研究的不够深入导致的。如果仅仅允许父母提起“不当出生”之诉,赔偿的是父母的损害,赔偿的财产归父母所有。虽然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但是很多省的《计划生育条例》都规定,如果第一胎是非遗传性残疾,允许生第二胎。父母因先天残疾孩子出生所获得的赔偿,不一定会用于这个孩子的教育和培养。尤其是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如果残疾儿童没有得到相应的损害赔偿,残疾儿童将来的特殊教育和支出就更可能得不到保障。
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对未成年人的财产范围和内容没有界定。台湾“民律第一条草案”中第四篇亲属法第60条的立法理由,将设置未成年子女财产制度的理由阐述得极为透彻:“夫论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之仪,似乎为人子者,不应私有财产。然近世欧美各国,推究人道,广其民曰公民,人子非父母所得而私,即人子之权利亦非父母所得而抑,虽在亲权之下,而其子或为亲属遗产之继承,或有对其子为财物之遗赠及赠与者,皆属法所不禁,此时为人子者,固不敢以财产与父母争,而为之父母者,若必尽收为己有,设使兄弟多人,异日平分父母之产,则本为一子之所独有者,而分析为众子之所共有,揆之法理,亦未为平。故各民法,多认为其子之特有财产,此亦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惟是子未成年,初无管理财产之能力,自应以行亲权之父或母管理之。”因此,我们认为,应当认可残疾儿童的“不当生命”请求权,赔偿所得作为孩子的特有财产,专门用于其将来的特殊教育和培训。
“不当生命”请求权合法化的困境与解决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基本上都不承认“不当生命”请求权的合法性。不承认的理由涉及很多方面,主要有公共政策方面的困惑、是否构成侵权以及如何界定损害赔偿的范围。
公共政策的考量
许多早期案件都把注意力放在公共政策问题上,认为“不当生命”诉讼将产生对流产的鼓励,相关的公共政策是在生命总是好于无生命的概念下思考“不当生命”诉讼的。在不当生命案件中,多数法院坚持原告孩子必须证明要不是由于过失医疗,他(她)的母亲本来可以选择不怀孕或者流产。而且,由于医生过失没有检测出基因缺陷导致的“伤害”或“损失”以及额外的照顾费用本身就构成了痛苦或者困难的生命。因此,法院在不当生命案件中就推定孩子的请求是由于他的生命本身是不当的,以及痛苦或者有缺陷的生命本身构成损害。基于此,绝大多数法院否定了不当生命的诉因,因为他们关注的是损害的要素,认为生命本身不能构成损害。持此论者假定生命总是好于没有生命和(或)事实上计算有生命与不存在相比的赔偿金是不可能的。
然而,流产的权利以及拒绝生命以避免痛苦疾病存在的权利都是宪法所保护的。有生命总是好于无生命,因此无论以任何代价都必须保存的观点——在许多案件中用来否定“不当生命”诉因的政策——现在已经失去了法律和公众的支持。
是否构成侵权
在审理英国“不当生命”第一案McKay v. Essex Area Health Authority时,“法院认为,在四个方面没有认可其合法的基础:第一,医生对胎儿的治疗义务不能扩展为终止其生命的义务;第二,承认该诉讼会危害生命的价值,将使残疾儿童的生命贬值到被认为不值得保留;第三,比较缺陷生命造成的损害和不存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第四,不当生命诉讼的胜利将可能不可避免地鼓励医生在有异议的病例中作出终止怀孕的建议。”关于因果关系,Stephenson L.J.认为将损害归咎于被告是不合理的。他坚持,“孩子的损害不是由被告造成的,而是由风疹造成的。”因此,主张医生的过失与孩子的损害没有因果关系。澳大利亚的普通法律和英国、加拿大及美国大多数州一样,认可父母提起的“不当出生”诉讼的合法性,而拒绝承认孩子提起的“不当生命”之诉。
德国联邦最高普通法院民事判例集86第240页(BGHZ 86,240)记载了这样的案例:由于负责诊疗的医生在一位女士怀孕期间没有察觉到她患了风疹,导致婴儿先天严重残疾。假如婴儿的父母知道母亲患病这一事实,他们就会决定采取终止妊娠的措施。母亲以生育困难(剖宫产)为理由提出痛苦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孩子以先天残疾为理由要求支付赔偿。联邦最高普通法院驳回了孩子的诉讼请求(见该案判例集第250页)。
我国对此类案件大多以医疗损害赔偿为由提起诉讼。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李天佑、张威、李雪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中,认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李天佑的出生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认可了孩子的父母的损害赔偿请求。但是,针对先天残疾儿童李天佑的损害赔偿请求,北京一中院则认为,“李天佑自怀胎受孕即患残疾,其残疾并非医院的过错导致。其请求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同时,本院认为,生命应当予以尊重,李天佑纵有残疾,但不能因身患残疾而低估其生命价值。残疾相对于健康确是一种缺陷,我们也深知李天佑将来面对人生的艰难,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超越人生之缺陷,感受生命的痛苦及快乐,认识生命的真谛。通过父母的抚育培养及自身的努力奋斗,使自己成长为一个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
因残疾出生的孩子本身提起侵权之诉,确实存在诉的主体、责任构成和法律政策上的诸多障碍,上文提及的各国法院的否定性理由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彻底否定孩子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也有失公允,因为孩子确实因为医师违反了产前诊断义务而遭受了反射性损害,在这一点上,与其父母所遭受的损害在性质上是一样的。[14]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也在逐渐转变对于“不当生命”请求权的态度。
法国最高法院于2000年11月17日在Nicolas Perruche一案中,撤销了巴黎上诉法院的裁决,首次准许了错误生命之诉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此案的案情和英国McKay案的实质几乎是相同的,但结果却截然不同。其理由是:(1)从医疗技术的角度来看,由于本案中的妇科专家和实验室在诊断母亲是否对风疹产生免疫力方面发生了错误,因此毫无疑问是有过错的;(2)由于“儿童生命质量降低了”,所以存在着损害;(3)由于原本可以通过堕胎予以避免的残疾导致了生命质量的降低,所以在医疗过错和损害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不当生命”之诉在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上,最大的困境是解决损害和因果关系的问题。
● 损害
对于未出生者的保护,通行的规则认为,孩子可以对由于出生前过失导致其伤害提出请求,是一般的医疗过失,其请求权是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不能诊断出已经存在的缺陷导致生出一个不正常的孩子被认为是独特的“不当生命”的诉讼。这种分析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除了出生前过失伤害案件,没有其它伤害会发生在胎儿身上。比较而言,对于“不当生命”的请求,潜在的前提是如果没有过失,缺陷仍然会发生在孩子身上,因为它在医疗过失行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不当生命”的理论至少部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上的,即医疗的介入并不能防止或减少既存的基因缺陷。然而,基因检测和作为介入因素的出生前医疗技术在迅猛发展。现在的早期检测能够检测出基因缺陷,就是提供一种机会,让母亲和(或)胎儿接受治疗来防止缺陷在出生后表现出来。其实,这些案件和出生前过失医疗案件一样,医疗过失和缺陷之间也存在因果关系。“正义要求吾人承认一项原则,即每个孩童,均应享有得以健康身心开始其生命之权利。”在这些案件中,“不当生命”的原告遭受的损害是失去健康生命的机会,而不是生命本身。
由于损害是构成过失侵权的因素,原告需要证明实际的损害或损失。这一原则内在的要求是,证明由于过失原告比他或她本来更糟糕。这一般不是意味着原告必须证明,作为过失的结果,他或她的存在,他或她的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更糟糕。相反,原告只需要证明的是,由于过失,他们在某些方面身体或经济上比他们本来更糟。如果过失也使原告在某些方面受益,这些利益也不会否定过失的认定,但可能在得到的利益上抵销损害。
● 因果关系
支持“不当生命”请求权的法官认为,“不当生命”诉讼可以在一般侵权法上取得成功,违法行为和因果关系是直接的。因为双方都承认如果有义务存在并且被侵犯,被告的行为显然是(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告损害的原因,而且如果没有过失行为这一损害不会发生。
首先,医师对于孩子是否有先天残疾负有注意义务。如果检测可能降临到胎儿身上的可预见危险的合理注意义务被履行;警示那些理性的人应做的危险;合理地来为病人提供建议和指导或者把病人送到可以提供建议的人那里,那么医师对孩子的注意义务就完成了。医生对孩子的义务,不只在不当生命中,而是在任何产前过失的案件中都是与对母亲的义务冲突的。但是,这一注意义务通常在产前过失案件中是被认可的,因此在“不当生命”中也应当得到认可。
其次,我国目前通说采相当因果关系说。即“无此行为,虽不必生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即足生此种损害者,是为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亦不生此种损害者,即为无因果关系。”在“不当生命”之诉中,如果没有医师的过失行为,孩子可能失去健康生命的机会,也可能不会;但是,因为有了医师的过失行为,孩子的父母通常会把孩子生下来,使得孩子受到上述损害。因此,医师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与孩子的损害是有相当因果关系的。
● 损害赔偿
“不当生命”请求权,究其实是损害赔偿请求权。其范围如何界定,也是一个难题。在McKay v Essex Area Health Authority案中,Ackner J 认为法庭无法来评估“不存在”,从而主张“不当生命”之诉无法得到损害赔偿。但是,在Perruche案中是这样讨论的,“不是因为出生而寻求赔偿,而是因为残疾¼¼因为他存在,问题不是他的出生而是残疾。”这些孩子的残疾导致了大量的医疗及其他费用,还有些案件中孩子生下来只是遭受痛苦,旋即死亡。而这些经济上的支出和生理上的痛苦都是由于医生的过失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使其不得不承受的。
在美国的Curlender v. Bioscience案中,法院允许孩子因其所受的疼痛和苦难要求一般和特殊的损害赔偿,并可得到惩罚性损害赔偿金。不过,Burns认为,“正如该观点的短寿所证明的那样,法院的判决走得太远了。”两年以后,加州高等法院审理了Turpin v. Sortini的“不当生命”案件,该案是一个先天性耳聋的孩子上诉的,由于医生对她姐姐耳聋的错误诊断剥夺了其父母不生原告的权利。法院认为孩子有权得到教育、训练的特殊损害赔偿,但不包括一般的损害赔偿,因为“要决定原告被有缺陷的生出来是否比不存在遭受更大的伤害是不可能的”。 美国在认可“不当生命”诉讼的四个州中,现在的司法观点都是特殊损害可以得到赔偿;但是,由于“不存在”的难以比较和评估损失难度的阻碍,不能获得普通损害赔偿。这就有点混合了大多数州所采取的立场。不过,这四个州的做法依然是值得称道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时,要注意医师过失行为对造成孩子损害的原因力。在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中,原因力规则被广泛采用,通常将其称为“损害参与度”或“医疗过错参与度”。原因力指的是在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共同原因中,违法行为和其他因素对于损害结果发生或扩大所发挥的作用力。相较而言,损害参与度是一个概括的概念,杨立新教授建议在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中,统一使用原因力的概念,保证侵权法概念和规则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在“不当生命”请求权中,孩子失去健康生命的机会这一损害结果,其实是由医师的过失行为和孩子的先天的残疾两个原因共同导致的。我们一方面要明确医师的过失行为确实是造成损害后果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清楚的将医师过失行为和孩子具有先天残疾这一非人力原因加以比较来确定医师的损害赔偿责任。
其实,历史上和现在对于“不当生命”理论的技术性法律分析是有缺陷的,经不起仔细的推敲。这种分析在两个基本方面背离了现有的侵权法政策和过失的方法论。第一,法院基于对侵权法的社会角色不完全和不准确的理解上,否定使原告恢复到受侵害前的状态这一侵权法的目标将不会使原告获益,因为缺陷在医疗过失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第二,法院用来确立和计算赔偿的方法严重背离了传统和现代的过失分析方法,拒绝承认清晰的经济损失和(或)否定法律上的一般赔偿金。尤其是从早期“不当生命”案件裁决以来,侵权法理论和哲学的演变是朝着建立在社会保障和成本转移基础上的损害赔偿体系转变的,这样,用来否定错误生命请求的分析模式就更缺少可辩护性。一种包括“不当生命”案件在内的医疗过失的一致的方法,将增强侵权法体系的正当性,并且与平等保护和正义的观念相契合。 2002年的研究资料表明,美国当时有28个州不认可“不当生命”的合法性,8个州立法规定不予法律保护;3个州允许该诉讼在普通法上得到救济,其中2个州通过立法确认了其合法性。而2005年的资料显示,美国有26个州拒绝提起该诉讼,4个州(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康乃狄格和华盛顿)确认其合法性。从数据的简单对比中,我们管中窥豹,可发现“不当生命”诉讼的合法有效性在逐渐地得到认可。
“不当生命”请求权的理论框架
对于“不当生命”的探讨,不论是否定还是肯定说,对其的研究都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理论。我们通过上文对“不当生命”请求权理论困境的研究和解决,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以期在理论上对其加以完善,在实践中为其提供理论支持。
不当生命请求权的主体
“不当生命”请求权的主体是,该儿童因为医师的过失行为在出生前没有被检测出具有先天残疾,而父母误以其为健康儿童被生产出来。医师的过失行为发生在孩子出生前,但是,过失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却是到了孩子出生以后显现出来。
加拿大最高法院审理Montreal Tramways v. Leveille案中,Cannon法官在肯定胎儿权利方面提出了下列理由,“诉因产生的时间是在遭受损害之时而非在不当行为实施之时。只有原告出生并感受到了身体残疾之时,她的要求赔偿的权利才得以产生。只有在出生之后,她才遭受了损害。只有在那时,她的权利才遭到了侵犯,她才开始拥有权利。”
按照德国联邦最高普通法院的观点,出生前损害的问题不在于胎儿是否具有有限的权利能力,而是在于对出世的孩子健康的损害(该判例集第49页):“胎儿的本质就是其最终能成为一个人而来到世间,其与出生后的孩子是同一生命体,责任法必须顾及这一符合自然规律的实施。因此,对胎儿的伤害必将及于该人出生后的健康,对此,加害人必须根据《民法典》第823条进行赔偿。”
我国台湾“民法”关于出生前侵害之损害赔偿问题,未设特别规定,王泽鉴教授认为原则上应适用第184条第1项前段之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者,应负损害赔偿责任。”此条所谓的“他人”,是指有权利能力的人。关于胎儿之权利能力之性质,计有二说:一是附解除条件说,认为胎儿出生前既已取得权利能力,但将来如系死产时,则溯及丧失其权利能力。二是附停止条件说,认为胎儿须待出生后,始溯及出生前取得权利能力。学者多采前说。我国民法对于胎儿的权利能力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为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我国立法对胎儿的权利能力采用的也是附条件解除说,肯定了胎儿时期即具有权利能力。因此,我国在《侵权责任法》正式实施之前,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先天残疾儿童就其未出生时医师的过失行为导致的损害后果,请求医师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不当生命”请求权的要件
“不当生命”请求权是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不当生命”请求权就要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 违法行为
“不当生命”请求权成立必须要有医师的违法行为。医疗保健机构在为育龄妇女和孕产妇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时,对育龄妇女、孕产妇及其胎儿均负有发现不利状况并提出医学建议的注意义务。医师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违反了注意义务,没有发现有关胎儿残疾的状况并给出应有的医学建议,医师的行为即违法。
● 损害后果
由于医师的违法行为,导致先天残疾儿童的出生,使得这一孩子失去了健康出生的机会。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要面临更大的痛苦和磨练,要付出比健康儿童更多的艰辛和努力,给孩子造成了损害后果。
● 因果关系
如果没有医师的违法行为,先天残疾儿童就不会出生,因为医师的违法行为,使得孩子的父母误以为孩子是健康的,而将孩子生产出来。医师的违法行为与孩子的损害后果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如果医师发现孩子存在先天残疾,并尽到了提醒和告知的义务,而孩子的父母依然坚持产下孩子的,孩子的损害与医师的行为就没有因果关系。
● 故意或过失
一般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中,医师的心理状态是过失,如果是故意的话,则构成了故意伤害的其他侵权行为。但是,在“不当生命”的侵权中,我们认为不排除医师故意的可能。
“不当生命”请求权的范围
按照侵权法的一般原则,被告应负责赔偿合理预见的各种损失或损害发生的一部分或由于疏忽造成的损失或伤害。疼痛,痛苦,医疗费用和无缘无故的照顾成本都是合理预见的各种损失或损害发生作为残疾人生活的一部分。按照一般的原则,有过失的医生将承担这些的损害赔偿责任。那么,如果要求的损害是原告的生命或作为一个整体(残疾人)存在,那么,无缘无故的照顾成本将无疑不仅包括特别的或额外的成本(因为残疾),而且还包括基本育儿保健费用,包括大量用于食品、衣着和运输的费用,因为这些抚养费也是作为原告残疾生命的一部分发生的。然而,在“不当生命”中,“生命”本身不是损害的组成部分,损害赔偿的范围将不包括抚养费,因为抚养费是归因于原告的存在,而不是残疾构成损害。
结语
因此,我们认为“不当生命”只能请求包括教育、训练在内的特殊损害赔偿。同时,我们认为,这些费用还要通过对医师过失行为和儿童先天残疾的原因力比较,来最终确定赔偿数额。 应当把造成“不当生命”损害后果的全部原因看做100%,把全部损害后果看做100%,将各个不同的原因进行比较,确定各个原因在全部原因中所占的百分比,就能够确定过失行为的具体原因力。把医师的过失行为和儿童本身具有的先天残疾两个原因力加以比较,我们认为,这两个原因对于“不当生命”的损害后果所起的作用基本相同,因此,可以认定医师的过失行为承担儿童的教育、训练的特殊损害的50%。
- 本文授權資料來源:医药健康报告
王丽莎
-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北京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卫生法学理事、中国医师协会医学人文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本科曾学习临床医学,从事医学法学交叉学科理论、实务工作11年。
- 电话/微信:15120007769
- 邮箱:liza52534@126.com
- AI醫療的倫理規範與責任釐清 12/8
- 醫療器材管理法的制度革新與風險治理 12/1
- 醫病關係的安全挑戰 11/26